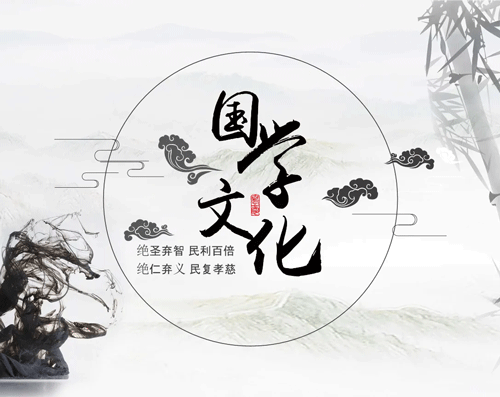鎌田茂雄:华严经讲话 一、沙漠绿洲中盛开之花——华严经
发布时间:2025-01-09 22:38:56作者:大悲沙漠之绿洲——于阗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县,为南接昆仑山脉之城镇。公元一九一三年时,称为于阗县;公元一九五九改为和田县。此即沙漠之绿洲——昔时之于阗。
和田县,为包括自昆仑山系北流之白玉河与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绿洲。因白玉河盛产白玉、黑玉河盛产黑玉而闻名。自河床所采收之玉,古来即为于阗之特产,西向至伊朗、伊拉克,东向则中国,为重要之贸易品。因贸易而令于阗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绢布,以及饰样华丽之地毯、褥垫等,颇受各国珍视。
于阗因位于东西贸易之要地而繁荣,更因吸收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独特之文化。伊朗系之琐罗亚期德教于此盛行,佛教亦传入,且建有佛寺。
据《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载,於于阗,人民亦重视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于六齐日时,必躬自洒扫,以谷物、果物供奉于祭坛。
于城南五十里处,有寺院名赞摩寺。即昔时罗汉比丘卢旃(毗芦舍那罗汉)为王塑造盆浮图之所。又佛足石上,明显的留有佛两足之迹。
于阗西向五百里处,有比摩寺、相传为老子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场。
如此盛传佛教之于阗国之废墟,现今于和田县城之南方约二十五公里处,有其古城之遗址,此即史书所谓之「西城」。遗址中残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筑用墙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约六公尺余,周围约六十公尺,四周散置无数泥塑之残片。石塔附近有房舍之遗址,为流砂所覆盖盖。此处曾发现泥塑之佛像头,可知此房舍为寺院之遗址。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曾于此寺院遗址中发现汉代「钱」之贮藏所,据称曾出土五铢钱(汉代钱之名称)九十余枚。
此寺院究竟为何名称?据称测,或为《法显传》所云瞿摩帝(Gomati)大寺。
绚烂一时之寺院与行像
老法显为求残欠之律藏,自长安出发之时为晋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一说公元四○○年),恰于鸠摩罗什抵长安之前,亦为《华严经》之译者佛驮跋陀罗(觉贤)长安安之前七、八年。
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嵬等,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现在甘肃省西宁,至张掖,又经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楼兰)。此国约有僧四千余人,为一佛教国,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显一行于此逗留约一个月,即向西北前进,约行十五日,至乌夷国(焉耆回族自治县)。乌夷亦为小乘佛教国,有僧四千余人。自此再经一个月又五天之行程,始达于阗。
依法显之记载,可获知公元四○○年前后于阗佛教之状况。于阗国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约数万名僧侣,研学大乘佛教。为约大于鄯善、乌夷等国十倍之大佛教国。每户人家门前皆立一小塔,虽为小塔,其高约二丈余。
此国中,为接待旅游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当国王得知法显一行将至时,特敕留于瞿摩帝寺,此寺为大乘之寺,约住三千名僧侣。食堂中之威仪,皆依戒律行事,人众虽多,却寂静无声,法显亦颇为惊叹。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发向竭叉国前进,法显为观此国之佛教仪礼——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谓行像,即将佛像安置于装饰华丽之花车上,游行于市区,供人瞻仰。此为佛诞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国,均以四月八日为中心而举行之。
于阗国有十四所大伽蓝,自四月一日起,即清扫道路、张灯装饰,并于城门上悬挂饰幕以为庄严。国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学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国王之尊敬,故于行像仪式时,均列队缓步于列之前。
行像之车辆,于城外三、四里处装置,其车为四辆车,饰有高约三丈余之御殿,七宝庄严,幢幡为饰。佛像立于车中,两旁为菩萨像,以金银装饰而成之飞天像,则悬挂于半空中。
行像之车抵城门约进步前时,国王即卸去王冠,着新衣,在裸足、捧香华之侍者随从下,出城门迎接佛像,国王顶礼佛足,为佛像散华、烧香。
当佛像抵城门时,于门楼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纷纷散花供养。
于阗计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结束时,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间,于阗城内皆为庆祝释迦佛之降诞而欢愉。
《法显传》中,又记载着于阗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于城西七、八里处。自创立以来,已有八十年历史。据云,系历三位国王之经营始完成。佛塔高约十五丈,堪称为一大塔。塔之建筑,以金银为主,并饰以众宝。佛塔之后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涂之。其间亦有装饰严丽之僧房。五世纪初,于阗之寺院,其堂皇、庄严,于此不难窥知。
向流沙去之法领与渡海而来之觉贤
於于阗佛教全盛之时,有一汉族之求法者朝于阗而来,其名为支法领。支法领至于阗时,曾因于阗之大乘佛教兴盛,以及大伽蓝耸立兴叹不已。支领自汉地至于阗,乃为求大乘经典而来。于国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养大乘经典。
支法领於于阗滞留时,风闻一重要情报,即于阗国东南三十里处,有险峻之高山,其中秘藏无数大乘经典,由国家派人守护,且严禁持出国境。
支法领得知此事,即恳请于国王,请将《华严经》让其持往中国流传。国王感于支法领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请。

此外,与法显同时出发,向印度求法之智严,迢迢抵达罽宾国。于罽宾国见到僧侣们戒律严谨之清净生活,衷心颇有感受,心想:中国之僧侣,有求道之意志,但却无真正指导之师,因此,于佛道乏人悟得。于是,智严即遍求罽宾僧侣,至东土教化。
时人告言「有佛驮跋陀罗(觉贤)者,生于天竺耶呵利城,姓释氏,代代崇佛。八岁出家,承佛大先禅师授禅法,现游化于此。」智严闻言,即确知此人乃弘禅、律于中国之人选。
佛驮跋陀罗者,即中国人所谓「觉贤」,此后,即以觉称之。
佛驮跋陀罗智承智严之恳请,遂决心远赴汉土,且决定不经丝路,改由海路至中国。
翻越葱岭以外,自印度经陆路至中国,有二种路线:一即经由喜马拉雅山脉,即现今之尼泊尔,再横断经西藏,通过青海省,抵达兰州,再至长安。一即经过缅甸,自云南入四川,再经长安而洛阳。此中,不论何路,均需攀爬雪山(万年积雪之高峰),因此,觉贤决意不行此路。
觉贤沿恒河南下,于恒河口附近登船。想觉贤当时所行之路,定为通商之道路。觉贤渡过缅甸,经由泰国,达东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岛而至河内、番愚(广州)。《高僧传》载其自交趾上陆,其意或谓沿途中之港口,或于缅甸南部上陆,横断印度支那半岛而达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国。
自交趾出发后,觉贤充分地发挥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岛附近,觉贤告知船宜于此停泊。然船主却以客船顺风难值,乃随风再行,约前进二百余里,忽遇风向逆转,船仍被迫返回小岛。时,又值顺风,众皆主张前行,惟觉贤反封。不久,乘风前进之船支遭颠覆。其后,于暗夜时分,觉贤告知现宜出发,却无从其言者。觉贤遂自解缆,仅自船前行。是后,凡逗留该处之船支皆遭海盗洗劫,或被杀害。
此事说明觉贤颇具有神异之能力,及通晓航海之术。船自交趾出发后直抵青州东莱郡。山东半岛之登州港,古来即为东亚各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发,理应于广州上陆,却远漂至山东半岛。法显亦然,返国时,亦显着于山东半岛青岛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觉贤与破戒之罗什
于登州上陆之觉贤,闻鸠摩罗什于长安,遂前往长安。其至长安之时,据推定当为公元四○六年或公元四○八年顷。
觉贤抵长安后,于公元四○一年至长安之鸠摩罗什甚表欢迎。自西域经凉州,而抵长安,当时飘泊之罗什,或想从觉贤处多少获些印度、罽宾等地之最新情况。然而,当时以罗什为中心之长安教团,与觉贤之间,似不能融洽相处。觉贤本为严守戒律、修持禅观之禅者。而罗什却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于罗什之教团中,觉贤似为不受欢迎之人物。罗什教团之僧众,颇受后秦国王姚兴之护持,然亦因而附会于政治权势,且常出入于姚兴之宫延内;相反地,从不步入宫中之觉贤,独自孤高绝俗,因此,颇令人感到不对味儿。被罗什及教团,包括政治权力者视为异端之觉贤,终于从长安被摈逐。
觉贤与弟子四十余人离开长安,自西域返国之宝云亦与觉贤同行。
觉贤一行蒙芦山慧远之厚爱,遂奔向芦山,承慧远殷殷款待,公元四一一年,觉贤于芦山翻译禅经。
约隔一年,觉贤下芦山,西行至江陵。公元四一三年二月,刘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觉贤同行,觉贤遂至东晋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时建康之僧众,颇仰慕觉贤孤高之风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领与觉贤之相会——六十华严之翻
自于阗求得《华严经》梵本返回长安之支法领,此时亦离长安抵达建康。闻觉贤住于道场寺,遂商请觉贤翻译《华严经》。觉贤欣然受请,始译于晋义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六月十日完成,费时二年又三个月,此即六十卷之《华严经》(晋经、旧经)。
是后,又比对梵本校订,于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时笔受者为法业。法业乃严持戒律之僧,通晓小乘佛教之教学,此次笔受《华严经》,实为中国人理解《华严经》之第一人,想法业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时,道场寺之僧众,颇惊叹于大乘经典《华严经》之内容迥异于过去之所学。究竟毗卢舍那佛是何种佛?所谓光明正大者又若何?过去之佛教从未如此说,甚至有人怀疑是否受琐罗亚斯德教之影响而说明?是否为真正之佛教?
通晓小乘教法之法业,于接触此一出奇之经典内容后,遂将其要旨撰写成书,即《华严旨归》二卷。法业乃欲汉土众人皆能理解华严教法,而热心撰写。至后时大成华严宗之法藏,于其着书中亦谓「大教滥觞,业之始也。」(《华严经传》卷二)
迄今为止叹未曾有之教法,《华严经》之梵本,若仅置于桌旁,或该受不敬之罪,因而考虑建堂祭祀,此即华严堂之建筑。位于道场寺一隅之华严堂,曾经入内参拜者,或许不仅支法领、法业二人,道场寺之僧众、一般之信众,参拜华严堂者相信为数不少。
获见于沙漠中之第二华严经——毗芦舍那罗汉与实叉难陀
公元四○○年顷,法显所见之佛塔,佛殿,僧尼完备之于阗王新寺,于经过二百余年后,玄弉亦翩然而至。玄弉至此拜访时,其寺名称为娑摩若寺。高百余尺之佛塔耸立着,灵瑞事迹时可闻悉,从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时,王城之南十余里处有毗芦舍那寺,为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赞摩寺,系于阗国之先生王为毗芦舍那罗汉所建。毗卢舍那罗汉乃来自迦湿弥罗国之比丘,常于林中入定。王为之建造伽蓝,并请其弘扬佛法。其名为「毗卢舍那」,恰与《华严经》教主同名。
据玄弉之记录,七世纪前半之于阗,国王颇敬重佛法,自谓即毗沙门天之末裔。国内有百余伽蓝,僧徒五千余人。与四○○年前同为大乘佛教盛行之国。据云,昔时如来曾至此地为天人说法。
牛头山之内亦有石室,有阿罗汉于中入灭尽定,系为等待弥勒佛下生。虽经数百年,但却不改其姿态。
唐人时之于阗,有名为实叉难陀(公元六五二——七一○年,学喜)者。时则天武后尊崇大乘,欲求《华严经》完整之梵本。据云于阗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于阗,求《华严经》之梵本及翻译者。时应机而来者即实叉难陀。
公元六九五年,始译于东都大遍空寺,武后亦自临御法座,撰写序文。菩萨流志与义净读诵梵本,复礼、法藏协助翻释。公元六九九年完成于佛授记寺。此即新译之八十卷《华严经》 (唐经)。
唐经与晋经两者比较,唐经文字较流畅,且内容亦自晋经之「八会三十四品」调整为「九会三十九品」,形态上较为整然。
公元七○四年,实叉难陀为探视衰迈之高堂老母,遂返回于阗;公元七○八年应中宗之请,又至长安;公元七一○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火葬后惟舌不坏,遂将之送返于阗。又于长安城北门之外,古燃灯台附近,建造七层宝塔,时人称之为华严三藏塔。
《华严经》为不可思议之经典。不论晋经或唐经,其梵本皆存于于阗。于阗乃大乘佛教兴盛、保存大量大乘经典之所。公元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译之四十卷《华严经》。并非完本,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卷《华严经》,系公元七九五年,南天竺乌茶国之师子王,将手书之《华严经》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华严经》之二种梵本皆在于阗被发现,此或显示着《华严经》系於于阗编纂之可能性颇大。且如前所述有关于阗之传说,所谓毗卢舍那罗汉,恰与《华严经》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绿州于阗,即今之和田县,虽昔时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废墟,在此地曾为信奉大乘之佛教国,且藏有多数大乘经典,其中之一即《华严经》。此经之梵本中历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于阗,一于公元四二○年、一于公元六九九年分别译成中国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