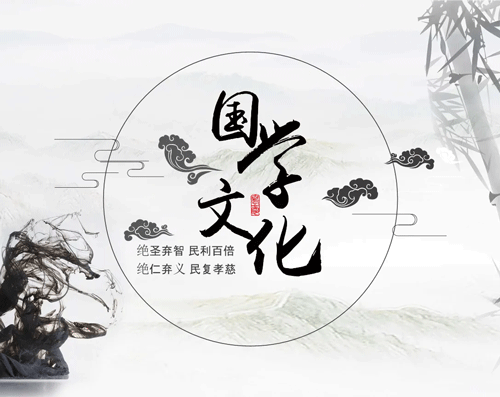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活佛转世
发布时间:2023-07-19 10:01:04作者:大悲佛教传入藏族地区的时间,晚于汉地、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尼泊尔等相邻地区和国家。因此,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和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似乎正因为藏传佛教汲取了四邻诸国家和地区佛教之精华,独领风骚,且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园林中大放异彩。
根据藏文史料,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当公元五世纪),由印度人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弟生将《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用品带到了吐蕃(注:参见《青史》(藏文)上册,64页,郭勋努白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许多藏文史书以此为佛教正法在吐蕃诞生之始。但鉴于当时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故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始。以松赞干布在位时(公元七世纪中叶)作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本土的开端比较妥当。至于松赞干布是否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目前还不能肯定,但他确实支持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许多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时,曾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的佛教大师学僧,在吐蕃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不少佛经。

实际上,松赞干布时期是古代藏族社会的大开放时期,又是大变革时期。松赞干布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改革或发展上,而无暇提倡佛教。佛教只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在吐蕃传播的,并没有当作唯一的宗教信仰加以特别崇拜。所以,从松赞干布至赤德祖赞(703—754年在位)期间,佛教在吐蕃虽然以时断时续的步骤一直传播下来,但这段时期的佛教在吐蕃没能真正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波教一统天下,佛教只是乘隙而入。值得一提的是,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开始,对于政治、经济,特别对文化领域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政策,这就导致了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波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波教烙印的佛教支派。
根据《巴协》等藏文史料,赤松德赞(77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才开始亲自参与并开展弘扬佛教的大活动。赞普首先派遣韦·意希旺波(又名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依靠赞普的强大后盾,在吐蕃举办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比如,堪布菩提萨埵向人们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缘起;白玛迥乃大师显示神通,调伏采波教的诸多凶神,还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藏族地区的公开传授。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桑耶寺于公元774年动工兴建,经五年于778年竣工,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同时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比丘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位藏族人首次剃度授比丘戒。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继“七觉士”之后,吐蕃本族的僧侣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寺院——桑耶寺的建成,以及吐蕃本族僧侣的产生,标志着佛教初胜苯波教,进而立足于吐蕃。
当时的桑耶寺不仅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又是译经场所。印度等地的许多大师和吐蕃学僧在桑耶寺里翻译了《律藏》、《经藏》、《密续部》等大量重要佛经。这是自从佛教传入吐蕃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译经活动。此外,吐蕃王朝对中亚的征服又导致吐蕃与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民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生活共同体,其结果是拉开了更大范围传播、发展、交流佛教的历史序幕。简言之,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由于得到了赞普的大力扶持,在吐蕃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赤祖德赞(815—841年在位)时期,是吐蕃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赞普敕令核订旧译佛经和编纂佛经目录,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拉萨河中游南岸创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九层金顶的乌香多宫殿(兼作寺院),它的“底部三层用石料,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筑成”(注:《西藏王臣记》(藏文)73页,五世达赖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其建筑形式十分壮观,“形如大鹏冲天飞翔”。赞普还拟定了僧侣在乌香多宫等寺院里进行时常诵念佛经的制度,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如有人反对佛教或轻视僧侣,便实施刑法来惩治。所以,吐蕃佛教在赤祖德赞时期出现空前盛况。至此,所谓的“藏传佛教”已经形成。
然而,不幸的是,佛教在朗达玛赞普(841—846年在位)时,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法难。朗达玛赞普亲自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抑佛运动,对吐蕃佛教、尤其对教团组织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僧众不仅失去了昔日朝廷的保护,而且还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僧众都不得不从寺院逃向民间,又重新加入世俗生活。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即指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算起)至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这段历史长达二百年之久。
此外,吐蕃王朝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也随着朗达玛的灭法为导火线而开始全面崩溃,一个衰败、瓦解的时代随之而来。很快吐蕃王朝分裂成一系列小邦,即现在许多著述中所说的地方割据势力。然而,佛教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禁废而寿终正寝,反之,政治上的大动荡给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朗达玛发起的灭法运动,不但没有彻底摧毁佛教在吐蕃的基础,还为继承和发展开辟了崭新、自由而广阔的前景。这从一个侧面又说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内已经赢得吐蕃人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广大低层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至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史籍里也没有一致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受比丘戒僧侣的大量出现和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是“后弘期”开始的重要标志。朗达玛的灭法运动,其后果主要是中断了传授戒律的连贯性。佛教一旦没有条件或资格举行常轨的受度仪式,就谈不上发展僧侣组织,如果佛教没有庞大的僧侣集团作为骨干或核心力量来发扬光大,也等于纸上谈兵。根据藏文史料,公元十世纪末在藏族地区又开始出现大批出家僧侣和重建寺院的热潮。由此可以将公元十世纪末视为“后弘期”的开端。
藏传佛教“后弘期”以诸派纷起、密教盛行,以及活佛转世的出现为主要特色,而且“后弘期”在传教范围之广大、群众兴佛之热情等方面,皆远远超过“前弘期”,其规模可谓空前。因此,“后弘期”成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时期。
从时间上看,藏传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是从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之间产生或形成的。
“藏历第一饶迥火鸡年(1057年),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嘉威琼乃修建热振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噶当派。
藏历第一饶迥水牛年(1073年),昆·贡却杰布修建萨迦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萨迦派。
藏历第二饶迥铁牛年(1121年),克朱穹波南觉修建香雄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香巴噶举派。同年,米拉日巴的弟子达波拉杰修建达拉岗布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达波噶举派。”(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第56页,东嘎·洛桑赤列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公元十五世纪初,最后一个宗派,即格鲁派产生。至此,藏传佛教的诸多互不隶属、见修各异的宗派,诸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包括四大支八小支)、希解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均已形成。
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整个过程中,宗教团体与世俗界之间的密切而互惠的联盟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双方都认识到互助的重要性。寺院僧侣集团依靠世俗权力,扩大各自的根据地或获取经济上的保障,而世俗政权又从僧侣集团那里得到有关思想舆论方面的支持。其结果,诸教派随着各自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参与世俗政权事务,而且还能左右地方政权。如元朝中央扶植萨迦派统一多年分裂的青藏高原,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证。从此藏传佛教界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诸教派不像以前那样在地方上寻求庇护,而是纷纷内向,开始靠拢中央王朝,寻找更强大的政治后盾,以便显赫一世。这个举措又恰恰符合中央王朝的意愿,因而藏传佛教诸多教派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过元、明、清中央王朝及至民国政府的赐封和关怀。单纯从政治的角度看,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皆为政治利益的产物,其政治势力的大小均为中央王朝所左右。比如,每次中央王朝的更替都会给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出现大动荡。
值得一提的是,格鲁派在藏传佛教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特别是1642年格鲁派取得西藏地方世俗统治地位后,其他教派受其威胁,许多宗派寺院无奈改宗格鲁派。从此格鲁派逐渐成为藏族社会上势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支教派。如西藏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这六大格鲁派寺院以及四大活佛系统即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旦巴。这一切都象征着格鲁派的权威和势力,并在我国藏、蒙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特别在文化生活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影响。
藏传佛教从公元十三世纪后期开始向其他民族地区传播,走出了单纯的藏族文化圈,给藏传佛教史上增添了一页辉煌的新篇章。今日国内,藏传佛教遍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为藏、蒙古、普米、裕固、土族、纳西等许多民族的绝大多数群众所信仰;在国外,诸如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及欧美的不少国家都有数量不等的信徒和传教中心或寺院。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已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佛教主要支派之一。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蓬勃发展的一大产物,也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对此曾有多人作过探讨,但其解释皆浮于表面化、而未能涉及到活佛的实质性问题。比如有这样的论述:活佛转世是以佛教的灵魂不死投胎复生的唯心观念与寺庙集团的经济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喇嘛教认为,修行好的喇嘛的灵魂是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的,而且能够通过另一肉体获得新生(注:1985年《西藏研究》第3期)。实际上活佛转世有其甚深的理论基础,佛教大乘经文中有“三身”或“三佛”之说。其“三身”或“三佛”皆指三种佛,即法身、报身、应身(化身)。如《大乘义章》卷十九日:“法者所谓无始法。”又曰:“后息妄想,彼法显了,便为佛体;显法成身,名为法身。”此处之“法”或“法性”,即是人们先天具有的如来藏、真心、本觉,以此为成就佛身之因,故又名法身佛或法佛。“报身”亦称报身佛或报佛,如“此真心体,为缘熏发,诸功德主,方名报佛”。此指以法身为因,经过修习而获得佛果之身,分为证知与享受所谓佛境的报身,以及为适应十地菩萨需要而呈现出来之报身。“应身”亦称“应身佛”,如“众生机感,义如呼唤;如来示化,事同响应,故名为应。”此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和需要而现之身,如释迦牟尼之生身等。
藏传佛教以“三种佛身”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并在具体的修行实践中不断探索或印证,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现,应身(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有若干个“化身”,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转生”或“转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附之物体,即“活佛”。简而言之,活佛转世是藏族高僧大德将佛教“三种佛身”学说结合藏传密宗的实际修炼而创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神秘文化现象。
基于佛教中的“三种佛身”学说,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临终前口嘱他要转世,因而开创了藏传佛教史上活佛转世之先河。之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事物相继被各教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卜卦、寻找、认定、教育、供养,以及信奉等一整套制度。目前,凡是称为活佛或喇嘛的高僧,究其根源或来历皆为诸佛菩萨的化身。显而易见,活佛的职责也要同菩萨一样,利乐世间众生。于是每一位活佛的最高理想是解脱自己,然后为了众生的利益,抛弃这种解脱而又重返人世。故活佛转世制度也不可中断。总之,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在佛教界、乃至世界宗教领域中的一大创举,也是世人所瞩目的一种特异的宗教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