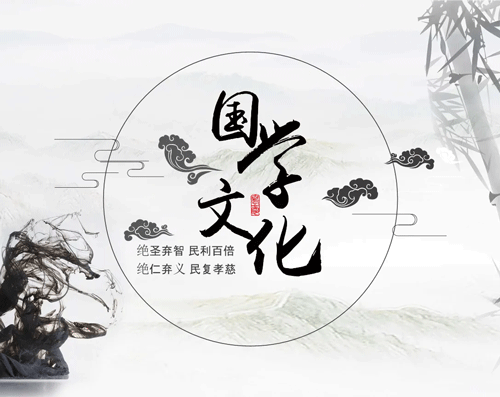金代的书籍出版与社会文化发展
发布时间:2024-11-26 02:51:44作者:大悲作者:李西亚(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
辽宋金时期,我国北方图书出版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的图书种类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图书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创新,图书印刷技术有所改进,印刷质量可与南宋相媲美,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众所周知,书籍是人类社会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图书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总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制度环境、文化教育、社会心理等的影响。因而,从传播学的视角来探讨金代图书出版与流通的背景与历程,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金代书籍出版兴盛的原因,亦能帮助我们认清其与金代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意义与作用显而易见。
女真人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在辽朝时期处于契丹族的统治之下,长期处在半游牧半渔猎的部落发展阶段。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后,阿骨打带领女真人在反辽斗争中迅速崛起,并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政权。建国之初的女真人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通过与汉族先进文化接触,意识到了文化对于巩固政权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集全国之力搜罗辽与北宋的图文书籍,网罗北宋的雕版印刷工匠,表现出了支持图书出版、进行文化传播的强烈愿望。清人赵翼指出:“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又以女直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直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8)因而,在公元1121年金对辽发动全面攻势时,太祖阿骨打特别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卷2)体现了对图书典籍与发展文化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金朝统治者还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推动图书流通、促进文化传播的政策。通过国子监刻印“五经”、十七史颁发各官学,自上而下传播汉文典籍。金世宗时还设译经所,大力倡导以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刻印出版,在女真人中以本民族文字来传播汉文化。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先后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等经史书籍15种。还特“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金朝还出版了一系列女真字童蒙书籍,如《女真字三字经》《女真字百家姓》《女真字姜太公书》等均有刊行。
随着金朝各方面统治制度的渐趋完备,科举制度也得以不断完善,在某些方面比辽甚至南宋还有所突破。金代的科举取士范围与前代相比有所扩大,允许奴隶放良后参加考试,取消了辽、宋时期巫医之家不得应举的规定,举人只要所犯罪刑不重的,可以听保应试,在任官员只有小的过失不至犯罪的,都可以参加考试,放宽了对应试者的身份和资格限制。金代还取消了科举取士的地区界限,客籍外乡者可以随时到所在州县应考。还在金世宗时期设立女真科举,为女真人开辟了一条新的入仕途径。金代独具特色的科举制度,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对科举的热情,使好学之风成为当时社会主流风俗之一。另一方面则使科举考试用书出现了较大的缺口,直接推动了相关图书的出版与流通。
女真族建立政权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我国家应天顺民,虽马上得天下,然列圣继承,一道相授,以开设学校为急务。以爱养人才为家法。以策论词赋经义为擢贤之首。天涵地育,磨砺而成就之”(刘渭:《重修府学教养碑》,见张金吾:《金文最》卷82)。在此背景下,不仅政府主持的官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私学及家庭教育亦兴盛非凡,形成了一种崇学重教之风。正如元好问所言:“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化民成俗,概见于此。”(《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卷32,《寿阳县学记》)如此崇文好学风气之下,教育与考试用书需求大增。民间书坊也大量刻印经史类考试用书,如宁晋荆家书坊主营科考类书籍,二十几年间不断刻印“五经”销售,即使战乱时期,也还将板片埋入地下,以备日后重新刊刻经营。
金人对宋朝一些名士的作品非常倾慕,故此类书籍及受其影响的图书在金代广为传播与出版。孔氏家谱《孔氏祖庭广记》广为流传,“凡缙绅之流,靡不家置”(张金吾:《金文最》卷14,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序》)。苏轼的作品在金朝也很受欢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流传颇广。金代诗人受其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影响,也创作出许多刚劲清新、通俗质朴的作品。“尔时苏学盛于北,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5)
金人对艺术的追求与欣赏,也推动了此类图籍的出版与传播。金代刻印的版画《四美图》描绘的是我国历史上四位不同时代的美人,分别是赵飞燕、王昭君、班姬和晋代石崇的爱妾绿珠。版画构图富于变化,人物衣袂飘飘,面容生动自然。《义勇武安王图》(关羽像),图像端庄肃穆,威武逼人。此外,金朝还开始了彩色印刷的尝试,这是元代套版印刷方法发明之前的重要发展,其代表彩色版画《东方朔盗桃图》成为我国印刷史上的重要作品。

宋金元时期流行一种说唱艺术诸宫调,是市民日常娱乐的内容之一。诸宫调在金朝的发展,为后来北方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年发现于甘肃黑水城的金代书坊刻本《刘知远诸宫调》证明了这一史实。此本不仅在金境内销售,还传到了西夏,说明此类书籍的出版数量较大,可以满足对外交流的需求。此外,据史料记载,金代还刻有《西厢记诸宫调》,只是今天还未见到刻本实物。但是可以推断,金代书坊出版了许多戏曲脚本,已经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书籍和书籍传播是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反之,书籍的产生与流通又促进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纵观金代的书籍出版史,其发展与繁盛也对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文化、教育及医药等发展的推动和对金代社会汉化进程的推进。
金朝建国以前,由于女真人尚未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使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记载几乎接近空白。因而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两宋相比,金朝的文化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金朝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和发展图书出版业,以改变文化落后的不利局面。金朝建国之初便开始着手编纂《祖宗实录》,此后陆续修纂了各帝实录,编纂了《辽史》《续资治通鉴》等史书,在史学编纂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许多经书的注解类著述开始不断面世,有力推动了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金代经学研究成就比较大的有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其中赵秉文的《易丛说》《中庸说》《论语解》,李纯甫的《鸣道集说》《楞严经外解》《老子解》,王若虚的《五经辨惑》等,均具有较大影响。
此外,金朝出版的医学典籍对中医学理论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刘完素、张从正等改变了传统以辛热之剂为主的用药方法,创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界的寒凉派与攻下派,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医书来阐述病理及治疗方法,如《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直格》等。金代医学著作成果丰富,还有《内经运气要旨论》《医方精要宣明论》《伤寒明理论》《针经指南》《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等。这些医书多次刊印,治病之方浅显易懂,在民间获得认可并广泛传播。如刘完素的医术之高明,从当时人对其所著《伤寒直格》的评价可见一斑,“治病之法尽于此矣”,“读之使人廓然有所醒悟”,“用药次第,悉皆蕴奥,精妙入神”,“虽古人不是过也,虽轩岐复生,不废此书也”。故而传播效果极好,“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张金吾:《金文最》卷42,杨威:《保命集序》)。
金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对外开疆拓土的过程,也是金代社会逐渐汉化的过程,图书典籍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女真族在灭亡辽宋以后,汉文图书典籍在上层的流通儒化了统治者的思想,促使他们采用宋朝的政治制度,认同并渐趋接受中原文化。金熙宗学会了吟诗作赋、交际礼节、象戏博弈,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逐渐汉化、儒化,“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大金国志校证》卷12)。海陵王完颜亮“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大金国志校证》卷13)。从而促进了女真社会的政治变革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加速了金代社会的发展和汉化进程,使之获得“一扫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的美誉。
由上观之,金代书籍出版的发展既是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结果,也是金代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助推因素之一,图书出版与传播和金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从深层次角度分析,正如向燕南等学者在《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中所讲,“公元10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认同传统”,“无论是在历史认同方面,还是在文化认同方面,都有着突出表现”。这一问题折射出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朝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通过支持图书出版积极汲取中原文化营养,并最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