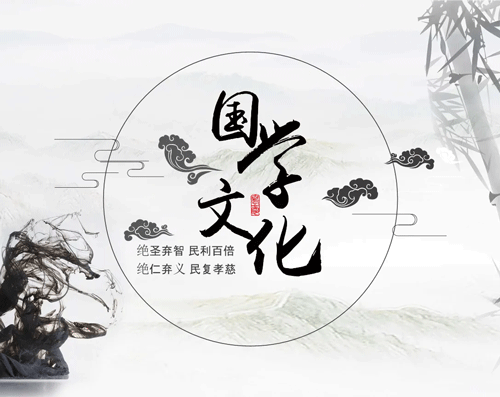高振农教授: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
发布时间:2024-06-25 12:05:29作者:大悲高振农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是批判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勇猛斗士,同时也是一个“畅演”佛教“宗风”、崇信佛学的人物。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少年时受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五岁受书”,“十五学诗,二十学文”(《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1981年版。以下凡引《全集》均只注篇名)。平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既学儒家经典,也读墨家、庄子的着作;既爱金石、算学、自然等学,尤好剑术和兵法。对张载、王夫之等人的哲学着作,曾潜心研习,学有心得。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竟悉弃旧学,主张变法维新。特别是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转向佛学,“昼夜精治佛咒”,研讨佛教哲理,逐步形成了以佛学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谭嗣同由原来反对改良而主张变法维新,并向民主主义前进,最后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经历着一条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由唯物向唯心倒退,后者由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前进。这种分析,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一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政治上进步,哲学上一定是唯物主义,相反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必然是唯心主义。关于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恩格斯就说过:“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谭嗣同则与之相反,他在哲学上特别是在北游访学以后,已是一个佛学唯心主义的崇拜者,但在政治上却成为一个“冲决”封建“网罗”的勇士。为什么谭嗣同在哲学上是一个佛学唯心主义者,却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闯将?他为维新、救国而献身的精神,与佛学唯心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想就这些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
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在本质上是落后的意识形态,但其中总有一些积极的思想资料,可以为一些先进人物所利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是说,唯心主义在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方面,有时会比唯物主义还要好些。当然,马克思也同时指出,唯心主义由于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但是却说明了在唯心主义体系中,是会有一些主观能动作用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为一些进步思想家批判地吸收,用以作为思想武器。谭嗣同之提倡佛学,崇信佛教,其目的正是想利用佛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作用,作为他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当然,亦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谭嗣同在运用这种唯心主义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些脱离实际,无〖BF〗视当时客观条件,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缺点。同时,我们说佛学思想是谭嗣同的哲学基础和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不排斥他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也不排斥他吸收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事实上,他是想用西学来充实佛学,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佛学唯心主义的。
谭嗣同提倡佛学,崇信佛教,并非是消极地逃遁空门,取得精神上的安慰,以求个人成佛。他想以佛学思想为武器,从中吸取力量,奋发有为,改造社会。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仁学》的目的中得到证明。《仁学》的创作,据他自称,是受了他的佛学导师吴雁舟的嘱托,为的是“畅演”佛教的“宗风”,“敷陈”变法之“大义”。他说:“去年吴雁舟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韩无首大善知识,将为香港《民报》,嘱嗣同畅演宗风,敷陈大义,斯事体大,未敢率尔,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分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体,已得数十篇矣。”(《仁学》)可见他写《仁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佛学,同时也是为维新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因为“畅演”佛教“宗风”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敷陈”变法之“大义”。
此外,谭嗣同之崇尚佛学唯心主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可看到他以佛学唯心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一斑。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在甲午战争后,思想为之一变,积极投入了维新变法活动。他自己也说:甲午之变,使他“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与唐绂丞书》)。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危难的局面,他大声疾〖KG*9〗呼:“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舐糠既及米矣,剥麻则又切肤矣”。又说:“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壮飞治事十篇?湘粤》)他一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决心致力于变法图强,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争战;一面向国人发出强有力的呼吁,认为不能“坐为异邦隶役”,不能丧失“自主主权”,应该起来救亡,用自强的办法来争民族生存的权力,争民族的完全独立,指出:“殷鉴不远,复车在前,吾人益不容不谋自强矣。”(同上)此外,他还痛恨清政府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号召大家起来打到纲常名教,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谭嗣同这种迫切要求维新变法的愿望,受到了来自封建顽固派的压制。在那十分困难的境地,他深深感到,维新变法迫切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去抵抗封建顽固派的压迫,维新变法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因此,他1896年的北游访学,既是为了宣传他的维新变法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为维新变法寻找思想武器。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还没有唯物史观的先进思想,就连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也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是在谭嗣同因为维新事业牺牲若干年之后,才翻译成汉文传入中国的。谭嗣同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物,和历史上许多追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一样,没有能找到当时世界上已经创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找到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佛学思想。就是这种佛学思想,他也不是随手拣来的,而是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才选定的。他对当时存在的耶稣教、民间的“在理教”与佛教作了种种比较,认为佛学理论比其他教派的理论学说要好,能够用以救中国。在他看来,耶稣教将来必将为佛教所代替,因此很欣赏美士阿尔格特的说法:“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兴者,其佛乎?”(《仁学》)对于“在理教”,他感到“其书浮浅,了无精义,乃刺取佛教、回教、耶教之粗者而为之”(同上)。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意义。只有佛教,理论上最玄妙。他还考察了佛学思想在日本维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日本变法之易,系惟佛教隐为助力”(同上)。谭嗣同对佛学思想作了研究对比后,天真地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认为是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他真诚地认为佛教唯心主义是“对”的,佛学是“灵”的,“教”能“保国”、“保种”。
在谭嗣同的心目中,佛学思想是当时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比拟的。他认为佛学无所不包:“佛法之大,固无所不包涵也。”(《仁学》)他在《致汪康年书》中还明确指出:“教能包括各专门之学,而各专门之学不能包括教。”在《仁学》中也说:“盖教能包政学,而政学不能包教。教能包无数,而无教不能包教。”这里的教主要是指佛教。他虽然也鼓吹孔、孟之道,并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总认为“佛能统孔、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西学皆源于佛学”。(《仁学》)他还认为,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佛书中早就有了。他说:“格致家恃器数术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同上)正因为谭嗣同把佛学思想看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他看来,佛教的地位是最高的,佛学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他说:“佛教纯者极纯,广者极广,不可为典要。惟教所适,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闻见,为人思力所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到,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并且断言:“今将笼众教而合之,……斯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同上)在他看来,佛教的威力也是不可限量的。他说:“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世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同上)佛学思想竟有如此之威力,所以谭嗣同要把它看做是“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的起源,只有佛才能解释清楚,所谓“无明起处,唯佛能知”。(同上)谭嗣同在这里把佛学唯心主义说得如此神乎其神,简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当然是过于夸大了佛学思想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如此推崇佛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目的不外乎告诉人们:佛学这种思想,高深莫测,威力无穷,运用它,可以御外侮,救中国,以此来增强人们的勇气,鼓舞人们的斗志,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进行变法维新。可见他是想利用佛学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来为他的维新变法事业服务。
二
谭嗣同作为一个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勇猛斗上,为了实现他维新变法的主张,从佛学中吸取了一些在他看来是非常积极、十分有用的思想。这些思想,简单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造了佛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
“一多相容”和“三世一时”,本是华严宗佛学里的相对主义思想。华严宗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它以“一”、“多”为例,说明空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说:“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多外无别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明知是一中多。”(《华严金师子章》)这是说,一和多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没有差别,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它又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为例,说明时间的流逝并非真实,尽在人们的一念中。它说:“百千大劫本由一念,方成大劫;既相成立,具无体性。”(《华严义海百门》又说:“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华严金师子章》)这是说,时间的概念也是相对的,一念之中就可以包括“三世”。这就抹煞了时间先后的客观差别和它的客观基础。谭嗣同却吸取了这种思想,把它看做是“天地万物自然而然之真理”,并加以改造和发挥。关于时间,他说:“今天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于过去未来而知之。然而去者则已去,来者又未来,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则固已逝之今日也。过去独无今日乎?乃谓之曰过去。未来独无今日乎?乃谓之曰未来。今日宜为今日矣,乃阅明日,则不谓今日为今日,阅又明日,又不谓明日为今日。……庸讵知千万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讵知千万年后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时’。”(《仁学》)关于空间,他说:“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于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则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体五官之分,四体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无数之分,……穷其数可由一而万万也。今试言某者是我,谓有一是我,余皆非我,则我当分裂。谓皆是我,则有万万我,而我又当分裂。……一切众生,并而为我,我不加大;我遍而为一切众生,我不减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同上》)。谭嗣同在这里,完全继承了华严宗的说法,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人与我、大与小、部分与全体等等范畴,统统看做是相对的。但他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于时间,他发挥说:“吾谓今日者即无今日也。皆自其生灭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而不息。则暂者绵之水,短者引之长,涣者统之萃,绝者续之亘,有数者浑之而无数,有迹者沟之而无迹,有间者强之而无间,有等级者通之而无等级。”(同上)关于空间,他发挥说:“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骨肉之亲,聚处数十年,不觉其异,然回忆数十年前之情景,宛若两人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续承承,运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从之哉?而势终处于不及。”(同上)很明显,谭嗣同在这里,已对“三世一时”和“一多相容”作了改造和发挥。在他看来,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迅速地向前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变化又是有规律的,任何人要想违反这一规律是办不到的,所谓“势终处于不及”。特别谭嗣同由此而引申出“日新”的理论,指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他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燠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同上)这些理论,道出了人类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

这种光辉的“日新”思想,为谭嗣同的维新变法事业,在理论上制造了有力的根据,在实践上成了变法的武器。但是,由于在思想渊源上与佛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使得他只能看到事物绝对变化的一面,看不到事物在变化中还有相对静止的一面,从而完全抹煞了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差别。他强调事物是永远不停地在生灭之中:“一刹那顷,已有无量佛生灭,已有无量众生灭,已有无量世界法界生灭。”(同上)他认为生和灭完全没有区别:“生灭即不生灭也”;“不生不灭,即生灭也”;“方生方灭,息息生灭,实未尝生灭”(同上)。在他看来,运动与静止也是一回事:“动即静,静即动,尤不必有此对待之名。”(同上)彼和此也没有不同:“有此则有彼,无独有偶焉,……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同上)最后结论是:“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同上)这里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因而使得他的思想尽管带有某种辩证法的因素,却始终没有能跳出相对主义的圈子。
(二)继承了佛学中的平等观念
谭嗣同从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要求打破官僚地主阶级垄断政权的局面,与他们平起平坐,因而极力宣扬平等,把平等作为奋斗的目标。他极力推崇佛教,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佛学中有平等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原始佛学在印度,一开始确实打起过“众生平等”的旗号,宣扬平等思想,并与婆罗门教的等级种姓制度进行了斗争。在他看来,要打破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就必须凭借佛学中的平等思想。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佛教是讲一律平等的。他说:“其在佛教,则尽率其君若臣与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属天亲,一一出家受戒,会于法会,是又普化使四伦者,同为朋友矣,无所谓国,若一国;无所谓家,若一家,无所谓身,若一身。”(《仁学》)这是说,在佛教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都是一律平等的,犹如朋友一样,没有上下尊卑之别。他也看到了当时印度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所谓“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为四等,上等者世为君卿大夫士,下等者世为贱庶奴虏,至不平等矣”。只是有了佛教以后,才提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现象的主张。所以他又说:“佛出而变之,世法则曰平等,出世法则愈出天之上矣,此佛之变教也。”(同上)他还认为,佛教的平等观念来源于佛教的大同思想。在他看来,“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钳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同上)。这些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印度的实际情况的,当时的印度社会,有严格的种姓(族姓)制度,一般称为四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两种为统治阶级,第三种姓包括农、工、商,首陀罗则是所谓最卑贱的人。这四种种姓,等级森严,极不平等。佛教不满意这种制度。才与之开展了斗争。在谭嗣同的心目中,中国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比之原始佛教时期的印度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大声疾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同上)他还进一步揭露,一切不平等现象,都是由封建名教造成的,而名教又是人“创造”出来的。他说:“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同上)在这里,谭嗣同运用了佛学中的平等思想作武器,向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三纲五常”,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认为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应该废除,其中首先要反对君主专制制。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同上)这是说,国君并非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当初是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既能推举出来,当然也可废除之,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谭嗣同在这里对君主专制制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还极力提倡男女平等,说:“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又说:“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中国虽亡,而罪当有余矣,夫何说乎!”在他看来,佛教是讲男女平等的。他说:“佛书虽有‘女转男身’之说,惟小乘法尔。若夫《华严》、《维摩诘》诸大经,女身自女身,无取乎转,自绝无重男轻女之意也。”(同上)
谭嗣同从佛教的平等观念出发,提出了反对君权、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要求,用以推进变法事业,从理论上讲,基本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在实践上也不会收到多少实际的效果。但在当时,对于揭穿“君权神授”的迷信,打击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瓦解封建论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冲决一切封建网罗来说,无疑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三)吸取了佛学中“我法两空”的“无我”思想
印度大乘佛学空宗有所谓“我法两空”的理论,它一方面把人类的自“我”说成都是“空”的,同时又把客观世界的万“法”也说成都是“空”的。中国佛学唯识宗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理论。在唯识宗那里,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人类自“我”还是客观世界的万“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一种内识变现出来的,所谓“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成唯识论》卷一)一切“我”、“法”都是“假说”的,是“识”所变现出来的,不是实有的。这本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十分错误的。但是谭嗣同却从中吸取了“无我”的思想,使之变成一种“为人不为己”的高尚的人生观,一种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谭嗣同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躯壳的变化,所以不必好生恶死,更不必对死产生畏怖的情绪。他说:“好生而恶死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FJF〗NC678〖FJJ〗也”(《仁学》)。既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应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正义的事业,一切为了利人、救人。所以他又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同上)还说:“念蠢尔躯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与唐绂丞书》)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一生,应该是除救人而外,别无他用,所谓“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同上)谭嗣同还认为,一个人要有救世之心,必须具备佛教所说的“无我”精神。他说:“怨天尤人,具以救世之心,未尝迫切,心乎救世焉,知有我哉?佛门之局量,勇犯无畏最大,然不能径致也,必慈悲为之根。慈悲则德几全矣。益无以致?必植基于平等;欲平等,必化异同,必无我相。”(《与唐绂丞书》)这就是说,要有救世之心,必须要有无我的精神。这种“无我”精神,贯彻到他的行动中,就是为了利人、救人,虽“杀身灭族”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矣’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以上种种,说明谭嗣同继承了佛教中的“无我”思想,并把它改造成为勇于追求真理和乐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一生热心于变法事业,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动摇,当变法失败,明知必死,却并不逃避,而是“竟日不出门”,“坐以待捕”,最后英勇牺牲。这就是佛学中“无我”精神的体现。
(四)发扬了佛学中的大无畏精神
谭嗣同深深懂得,要冲决封建网罗,实行维新变法,必须要有一种勇猛、精进的大无畏精神,用以武装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的信心。在他看来,佛学是最提倡大无畏精神的。他说:“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无畏有五:曰: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仁学》)这是说,佛本身就是大无畏的化身,而且在各方面都提倡“无畏”。他还认为佛教的“精意”就是所谓“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因此,只要能信仰佛教,就能得到这种大无畏精神,所谓“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同上)。佛学中的大无畏精神,使谭嗣同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喊出了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切网罗都应当冲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正是这种豪迈的气概,才使他的《仁学》能“写出数千年之祸象”,能“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也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才使他敢于反抗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压迫,并向之提出挑战:“嗣同等如轻气球,压之则弥涨,且陡涨矣。”(《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二》)谭嗣同的这种大无畏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变法实践中。当变法失败,明知必将遭到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镇压,他不仅不逃避,反而庄严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表现了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到了狱中,还题诗于狱壁:“我自横刀向天笑”,显示出他对反动势力毫不畏惧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直到临刑前还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声音。这一切,都说明了佛学思想中的大无畏精神,在他身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这种精神,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怀念和尊敬。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就曾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座侧,并满怀激情地在遗像上题词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续起志勿灰。”(邹鲁:《邹容略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42页)就连青年时代的MZD同志,也对谭嗣同异常敬仰,曾对蔡和森等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引自《张昆弟烈士日记》,见《湖南革命烈士传》)
总括来说,谭嗣同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经他改造过的佛学思想作武器,发挥了佛学中的积极因素,向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猛烈的攻击,对维新变法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最后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客观上成了否定改良、导致革命的桥梁,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佛学唯心主义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好的思想武器。虽然它也曾给予人们一种精神力量,使得一些进步人士能够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一心为了维新事业。但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使维新事业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单靠佛学中的主观精神力量,确实是“无力回天”的。特别是谭嗣同片面强调精神作用,即所谓“心力”的作用,把佛学思想看做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就必然使他只重于几个人的个人奋斗,幻想出现一个开明圣主,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在维新变法活动中,他虽也曾考虑发动哥老会进行武装斗争,“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之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急之用”(《戊戌变法资料》第4册,第90页)。但只是想利用一下,并没有作为真正的依靠力量。因此,当他接到光绪皇帝召他进京的“诏书”时,就非常兴奋,写信给其妻李闰,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致李闰书一》)。表现出他把变法的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开明圣主光绪皇帝以及他们几个维新派人士身上。此外,他也吸收了佛学中一些消极的思想。例如他在谈到“灵魂”时曾说:“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着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仁学》)这明显将佛学思想作为精神枷锁,诱使劳动人民安于现状,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要起来反抗,达到麻痹人民斗志的目的,其消极作用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