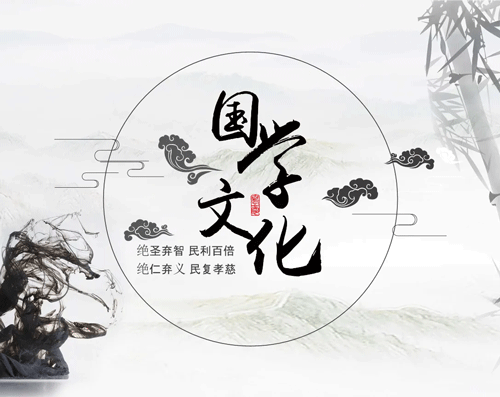情欲解放,怎么解放?——节欲、纵欲与离欲
发布时间:2024-01-23 12:26:41作者:大悲情欲解放,怎么解放?——节欲、纵欲与离欲
释昭慧

在宗教伦理学上,各宗教对情欲与婚姻的看法有异有同。在此但举基督宗教与佛教为例。两者的相同处是:都赞同依婚姻来规范情欲(亦即适度的“节欲”)。不同处是:基督宗教将情欲范限在互允贞洁之婚姻,把它当作是天主应许给人的一种“圣事”;反之,非婚姻关系的情欲,当然就是“罪恶”。若从佛法以观,欲界众生都有情欲;无论是“情”还是“欲”,其根源不外乎是“自我爱”——“欲”来自生理的需求(是“自体爱”的一种),“情”则填补了生命中自我实现的缺陷(是“我所爱”的一种)。情欲既无关乎神圣,亦无关乎罪恶,只不过是一种非善非恶的“动物本能”而已。
男女两人相互间的“忠贞”承诺,是情欲世界里双方相互系着(互相占有)的一种心理需求。一方倘有不贞,对配偶乃至子女,自然会带来极端强烈的痛苦。仁慈之人不忍任何人因自己的行为而受苦,所以除非他/她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否则无法不将其导致配偶、子女精神痛苦的“男欢女爱”,纳入道德层面的考量。此所以佛教虽系“无神论”,未视婚姻为根源于神的“圣事”,却依然在“护念众生”的前提下,要求在家佛弟子节欲——实践“不得邪淫”的根本戒律,男子、女人都不例外。
道德或法律层面规划出来的“一夫一妻”制度,虽顾及了“护念配偶心灵”与“善尽双亲责任”的理想,但无论于“情”于“欲”,都很难真正全面落实。于情,当宿世因缘深厚或心灵极相契合的异性出现在婚后,此时除非道德感强烈或定力深厚,一般当事人很难抗拒这种致命的吸引力;于欲,当贞洁的要求定调在“子息血统的纯正”时,它很难不沦为单方面的道德要求。于是乎,走马章台的男子被视作“风流倜傥”,纵情恣欲的女人却被视作“水性杨花”。
话说回来,“互允忠诚”的婚姻思维,固然带给女性比男性更多的文化束缚,但也并非对男子毫无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力量。贵为驸马的陈士美在包公的虎头铡下断命,这似乎意味着:通奸罪也不纯然是为羞辱女性而存在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万恶淫为首”,多少还是悲悯着那些一生相夫教子,到头来“色衰爱弛”,又无独立生活条件的女子,为她们的处境,提供一些舆论或司法层面的保障。
热衷于“情欲解放”理论且身体力行的女性,她们认为如此可以挑战父权意识对女性情欲的禁锢。然而情欲受压制的绝不只是女性;女性情欲解放,或可对治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却无补于自己受到情欲热恼之所奴役的不自由。
原来,情欲这种动物本能,虽然非关乎善恶,但深层审视其本质,它还是有一种“覆障清明”的作用——情令智昏。在佛法中归纳情欲为“有覆无记”——无记,在道德上属非善非恶的中性;有覆,是于心性的解放有所遮蔽,而且由此也会进一步发展出麤分的烦恼。
大凡感官所带来的快乐,都带有一种类似毒品“容易上瘾”的诳惑性(当然不似毒品那般危害剧烈)。快感无法持久,所以不是需要加重刺激,就是需要变换花样。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他可真洞烛了“五欲”的本质!
情欲虽属动物本能,但却有极大的个别差异。有人可以“但取一瓢而饮”,有人却非得要时时“转换口味”不可,这就不是“本能”或“天性”所可概括解释的,只能说是“习以成性”。纵情恣欲,无形中会加重感官的刺激需求,使自己反而增加“心为形役”的大患——本求解放而反成情欲奴仆,这是无论男性或女性的“情欲解放”者皆可深思的课题。撇开“道德考量”不说,即使站在“利己原则”的立场,都要慎防这种后果。唐伯虎点秋香,秋香之前已追求了好几个,秋香之后依然还追求好几个。唐伯虎快乐吗?怕是时时都要尝受“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情欲热恼之苦吧!
还有,虽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情欲较诸饮食,须戒慎者犹甚。因为饮食是无情物,可以任人支配;情欲则往往关涉到第三者,不是单方面的意志所可决定的。“欲”的解放,是否可连带改变“情”方面“我所爱”衍生的占有欲与妒忌心?倘若情欲解放只是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要留意的是另一方在“情感牵系”的无明盲动中,所可能导致的不幸后果。数年前发生的清大女研究生杀情敌案,就是一个悲惨的案例。
自我爱所衍生的情欲,是个治丝益棼的无解课题。佛教出家的“梵行戒”(“离欲”规范),理由即在于洞彻“情”与“欲”的双重系缚及其衍生的苦难,让修行人学习着以定慧之力,不受制于形体的情欲热恼,不受制于他者的情枷爱锁。倘能由勉力学习而渐臻乎至境,从情欲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或许才是真正的“情欲解放”吧!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