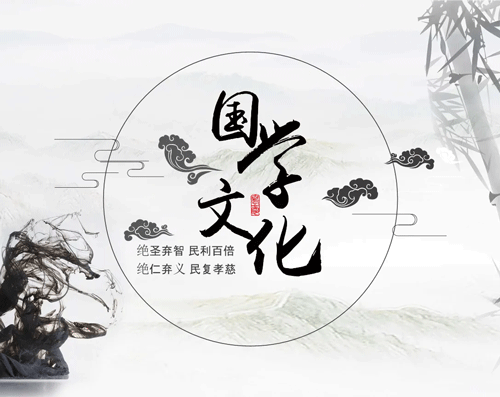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
发布时间:2023-07-30 19:27:53作者:大悲
一、大乘佛教的兴起
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内部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运动,对佛教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它在印度的兴起的历史,并不明朗。现代学者多以为它的兴起,大抵是在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一世纪。若追寻其渊源,则可更推前至佛灭后一世纪。在那个时期,佛教分裂为十八个或更多个学派,各有其特异的教理。其中的十一个学派,被视为保守的正统者;这正统即后来所谓“小乘”之意。其余的七个学派,由大众部(Mahasanghika)领导,表现较开放的态度。这大众部便是大乘佛教的发端。
在思想上,大众部一方面批评保守者的阿罗汉(arhant)的狭隘的理想,一方面发挥空的义理,认为真正的佛陀是超现世的,历史的释迦牟尼不过是他的示现而已。他们又提出菩萨(boodhisattva)的理想人格,认为菩萨的道路,是人人可行的。
一个学派的思想特色,与其兴起的真正的原因,自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对大乘佛教兴起的真正原因,有很多的知识。不过,抗塞(E。Conze)以为,有两点是可确定的。其一是阿罗汉的理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二是在家信众的压力。关于第一点,阿罗汉所表示的独善其身的出世的理想,在佛灭三、四百年后,已渐失去其魅力,也越来越少僧人达到这个目标。代之而起的,是菩萨的理想。关于第二点,人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与法(Dharma)齐平。出家僧众不再单独享有被尊崇被重视的权利。而在在家信众中,也出现不少杰出的人物,经典中的维摩诘(Vimalakirti),即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佛教的宗教意义,已不能再拘限于僧人与僧院方面了。在家信众开始积极参与种种的宗教活动。(注1)
随著宗教的发展,思想也渐趋成熟。由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三世纪,不少大乘经典先后出现。最先出现的是《般若经》(Prajnaparamita-sutra),跟著有《维摩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法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utra)、《阿弥陀经》(Sukhavativyuha-sutra)、《十地经》(Dasabhumika-sutra)等初期大乘经典。此中自以《般若经》为代表。此经最初由少量渐次附加,至七世纪左右而成一大丛书。其空的思想,一般认为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
其后有南印度出身的龙树(Nagarjuna),在哲学方面发挥这空的思想。他著有《中论》(Madhyamaka--karika)及《回诤论》(Vigrahavyavartani),批判部派小乘的谬见,建立中道观,而名之为缘起、假名、空。
龙树以后续有大乘经典出现,如《涅槃经》(Mahapari-nirvana-sutra),《胜经》(Srimaladevi-simhanada-sutra)、《解深密经》(Samdhi-nirmocana-sutra)、《楞伽经》(Lankavatara-sutra)。其中的《解深密经》的唯识说,有弥勒(Maitreya)、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等人发扬,其分别代表作为《大乘庄严经论》(Mahayana-sutralamkara)、《摄大乘论》(Mahayanasamgraha)及《唯识三十颂》(Trimsikavi jnap tima tratasi-ddhi)。其主旨是以识来解说世间现象。
二、关于“大乘”名称的由来
“大乘”这个名称。按“大乘”自是与“小乘”对说,而有其意义。“大乘”的相应梵语是“Mahayana”,是大的车乘或行程之意;“小乘”的相应梵文为“Hinayana”是小的,低等的车乘或行程之意。说小乘,显然有贬抑之意;相应地,说大乘,有显扬之意。实际上,“大乘”是那些后来的持较开放态度的佛教徒的自称,他们称那些原来的保守的佛教徒为“小乘”。后者从未自称为“小乘”。他们也不喜欢被称为“小乘”;他们原来是属于上座部(Theravada)。现代的佛教学者,不管是欧美的、日本的,抑是印度的,都以《大、小乘》之名,分别指那较开放的与较保守的派系,但这称呼是中性的,并无显扬或贬抑的意味,也不表示要赞成大乘,反对小乘之意。至于现代的上座部信徒,则仍不喜被称为“小乘”。
实际上,“大乘”一名的渊源,可上溯至原始佛教。汉译《阿含经》便在多处提到这个名字。如《长阿含经》(Digha-nikaya)谓
“佛为海船师,法桥渡河津,大乘道之舆,一切渡天人。”(注2)《杂阿含经》(Samyutta-nikaya)谓“阿难,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注3)此外还有多处不录。在佛之世,佛教徒当然未意想到尔后大、小乘佛教的分途发展。《阿含经》用“大乘”之名,大抵指佛的教法,而含有尊崇之意。这“大乘”自不同于尔后大乘佛教的“大乘”,但亦非全不相通。大乘佛教自有其发展,但其基本教理,并不远离佛的本意。
附带一说,“小乘”一名,亦见于《阿含经》中。如《增一阿含经》(Anguttara-nikaya)谓:
“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非小乘所能知。”(注4)这样说小乘,自有贬损之意。
三、现代学者论大乘佛教
以下我们检讨现代学者论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首先看铃木大拙的说法。铃木给大乘佛教下了一个定义,谓:
“大乘佛教由一种进取的精神所激发,在不违离佛陀教法的内在的精神下,扩展了本来的领域。另外,它把其他的宗教的哲学的信仰,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因为这样可使不同性格和智能的人得到解救。”(注5)在与小乘的对比下,他认为大乘佛教较自由和富进取性,但在很多方面都有形而上学意味,和充满思辩。(注6)不过铃木并不大强调大小乘的相异处,他认为这种相异并不是质的相异。这种不同只在于两者的取向而已;大乘要开拓宗教的自觉,扩展知识的范限;小乘则要力求保全僧院的律则和传统。他认为两者都从同一的精神出发,走同一的道路。(注7)
铃木这样论大乘,自然是对的,但显然太空泛,使人难以捉摸。不过,他总给人一个印象,即是,大乘有较宽的襟怀,要解救较多的人。这与他较后提出大乘是菩萨(bodhisattva)的佛教一点,很能相应。他说大乘是菩萨的佛教;而独觉(pratyekabuddha)和声闻(sravaka)则被大乘行者视为小乘之徒。(注8)
说大乘佛教,决离不开它的主角,这即是菩萨。抗塞在这方面,便较铃木大拙为具体。他说大乘佛教的首要之点是,它是一种生活之道,伴之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这即是灵性的完美(spiritual perfection),和能使人达致这灵性的完美的步骤。(注9)他所说的正是菩萨。灵性的完美即是六种波罗蜜多(paramita);那些步骤即是十地(bhumi)。这两者是菩萨实践的主要内容。在这两者之中,抗塞特别重视波罗蜜多。他说菩萨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要破除自我。自我是成佛的障碍,要破自我,是很不容易的。他说菩萨为了达致这个目标,采取两面的做法:在行动方面自我牺牲和无私服务;在认识方面渗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由此抗塞提出菩萨必备的两个条件:慈悲(compassion)与智慧(wisdom)。(注10)他说这两者的结合,有赖于六波罗蜜多的实践。(注11)
抗塞的所论,有进于铃木大拙之处。理由是,他不如铃木般空泛,却具体地把大乘规定到菩萨方面来;而在菩萨方面,他更把焦点置于波罗蜜多上。据《般若经》,波罗蜜多是菩萨的六面实践,所谓六波罗蜜多。这即是:布施(dana)、持戒(sile)、忍辱(ksanti)、精进(virya)、禅定(dhyana)、智慧(prajna)。前五者可归于慈悲,最后的智慧,则特别指空之智慧,即观诸法无自性空的般若智,藉此可渗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这六波罗蜜多并不是并行的,而是以般若智统率前五波罗蜜多。这点在《小品般若经》(Astasahasrika-prajna-paramita)中说得很清楚。(注12)
就上所论,在慈悲与智慧之间,抗塞似乎较重智慧。但大乘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或菩萨之所以能成为宗教的理想人格,似应以慈悲为重。这慈悲的要点,可以不舍弃世间一意概括之。
抗塞以菩萨来说大乘思想的特色,固甚具体切要。但是否全无问题,则仍有商榷之处。关于这点,下文继续讨论。
以下我们看平川彰论大乘佛教。平川彰首先把菩萨拆分为几个项目:“菩萨”观念、六波罗蜜多、十地。然后强调:这几项都不是大乘所独有,在此之前已出现了。即是:“菩萨”观念已出现于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中;六波罗蜜多的教理,已显现于《大事书》(Mahavastu)与《大婆沙论》(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中;而十地思想的萌芽,亦可在《大事书》中见到。(注13)平川的意思似是,单凭菩萨一点,不足以规定大乘思想的特色。
在另一方面,平川特别强调《般若经》的空的思想。他以为,《般若经》本著无所得的立场,使空的思想深刻化,而成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立场。由空使人想到空智(般若);他以为,基于这空而来的空智,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特征。《般若经》本著空、无所得的立场,而说方便,以进于社会的救度。在以社会为目的的运作中,有自己的解脱在。这点与小乘佛教不同,后者只谋求个人的救度。他并强调,菩萨的六波罗蜜多与十地的修行,若建基于这空的思想之上,便即改观,立场也变得不同。(注14)
四、大乘佛教的空论的特色
平川的说法是不错的。“空”是佛教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大、小乘对它的看法,不尽相同。大乘的空论,确有其特色;它的特色也应可表示大乘思想的特色。以下我们即以《般若经》为代表,看大乘佛教的空论。
笔者在拙文“般若经的空义及其表现逻辑”(注15)中曾表示,《般若经》的空义,是以无自性来规定;它和现象世界的关系,是不偏向舍离,相当重视世间法。这是与小乘不同之处。关于不偏向舍离一点,其明显表示,在于《心经》(Hrdaya-sutra)的名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色空相即,实显示《般若经》要本著现象世界是无自性因而是空这一基本认识,与不离现象世界的基本态度,来显示现象与空之间的互相限制、相即不离的关系。这不偏向舍离一点,也极其显明地表示于《小品般若经》中,所谓《不坏假名而说实义》。此中“假名”即指一般的世间法,或现实世界。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不偏向舍离即是不舍世间,这是《般若经》以至大乘佛教的空论的特色。有关其他问题,请参看上面所提拙文,此处从略。
对于《般若经》的空论的这个特色,从华严宗的法藏世界看得很清楚。他抨斥小乘教“即色非空,灭色方空”的狭隘立场,而提出“色即是空,非色灭空”。即是说,空并不妨碍世间法;空即在世间法处成立,不必要灭去世间法,才有空。(注16)不必要灭去世间法,即涵不舍世间之意。(注17)
五、大乘佛教论佛身
由上面所论,我们似可建立初步的看法,以大乘思想的特色在不舍世间。这主要是显示于其空观中,菩萨的实践,自然也有这个意思。他的智慧,其对象即是这空观;他的慈悲,也以不舍世间为基础。一般所谓菩萨“留惑润生”,便是这不舍之意。小乘后期纵有菩萨思想,自不如大乘般成熟。至于铃木大拙所说大乘有较宽的襟怀,要解救较多的人,这些人总是在世间的。故铃木论大乘,亦不离开不舍世间之意。
不舍世间是一种精神方向,生活态度。这方向或态度亦显示于大乘佛教的其他重要观念中,如佛身、真如与如来藏。以下为省篇幅计,只择佛身来论。
关于佛身,通常是三身的说法。这即是,佛基本上指释迦牟尼,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又是最高真理的觉悟者,故他有物理之身,也有精神之身。另外,为了普渡众生,他不时出现于世间,故又有示现之身。示现之身又可示现为佛陀,而成一个历史人物,故这示现之身又可与物理之身结合为一。在此之外,又有佛自受乐的身。因此而有三身。
物理之身即色身,指在历史中出现的佛陀。这是大家都能了解的。法身则指那普遍的精神,在历史的佛陀中显示出来。《阿含经》已说到法身。如《杂阿含经》谓:
“如来之体身,法身性清净。”(注18)《增一阿含经》谓:“尊者阿难作是念,如来法身不败坏。”(注19)又谓:
“肉身虽取灭度,法身存在。”(注20)故初期佛教,大抵是二身(色身、法身)的说法。自后大乘佛教兴起,乃有受用身及变化身的提出。受用身指佛享受佛法的乐趣时的身,也是专为对菩萨说法而示现的。变化身则是佛陀为了救度众生而示现出来的种种变化的身体。其最明显的莫如在历史中真正出现的释迦牟尼。由是便有三身之说:自性身(svabhavika-kaya,即法身)、受用身(sambcomika-kaya)、变化身(naimanika-kaya)。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变化身。它的成立是由于佛陀为了救渡众生。这众生自是世间的众生。这便透露不舍世间的涵意。这种身相当于较早期提出的三身(法身、报身、应身)中的应身,所谓“应”,是佛陀对世间的需求的回应。此中很有其积极的意义。唯识学派以变化身是成所作智所现,这益显示它与世间的密切相连。因成所作智是成办世间种种度生事务的智慧,是世间的智慧。
六、大乘经论论大乘佛教
以下我们看大乘经论自身如何论大乘佛教。这样看起码可以让我们知道大乘经论的作者如何自觉地理解他们自身的思想。这或许可以补本文开首说我们不能充分知道大乘佛教兴起的真正原因一点的不足。
首先看《法华经》。该经基本上是通过与小乘作比较,来论述大乘。该经谓:
“若有众生,内有智性,从佛世尊,闻法信受,殷精进,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声闻乘。……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殷精进,求自然慧,乐独善寂,深知诸法因缘,是名辟支佛乘。……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来知见、力、无所畏,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得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注21)此中论小乘的要点是“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及“乐独善寂”;论大乘的要点则是“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对比起来,小乘的舍离世间的精神或态度,与大乘的不舍世间的精神或态度,非常明显。
以下看《大智度论》。该论基本上亦是通过与小乘作比较,来论述大乘。该论谓:
“佛法皆是一种一味,所谓苦尽解脱味。此解脱味有二种:一者但自为身,二者兼为一切众生。虽俱求一解脱门,而有自利、利人之异。是故有大小乘差别。”
(注22)据《大智度论》,大小乘都有同一的目标,这即是解脱。但两者的做法不同。小乘是自利,只为自身;大乘则是利人,兼为一切众生。自利是把自身与世间分割开来,这便是舍离。利人则是把自身与世间结合在一起,视利人即是自利,这便是不舍。
另外,《大智度论》又以大慈悲心的有无,来判分大乘与小乘。小乘无大慈悲心,大乘有大慈悲心。(注23)这大慈悲心是表现于利人的行为中的。
《大智度论》更就智慧言,说小乘的智慧浅薄,不能深入诸法,故不说“世间即是涅槃”。大乘的智慧则深厚,能深入诸法,故说“世间即是涅槃”。(注24)这“世间即是涅槃”的说法,与《心经》的“色即是空”的说法,是同一思路;都是肯定现实的世界即此即是真理之意。世间即此即是涅槃,故不必舍世间以求涅槃,涅槃的理想即在世间中。不舍世间之意,至为明显。
以下看《大乘庄严经论》论大乘佛教。该论谓大乘佛教有七大义:
“缘、行、智、勤、巧、果、事皆具足,依此七大义,建立于大乘。”(注25)所谓大义,即不同于小乘的特别殊胜的义理。这七者是缘、行、智、勤、巧、果、事。无著解释这七大义谓:
“若具足七种大义,说为大乘。一者缘大;由无量修多罗等广大法为缘故。二者行大;由自利利他行皆具足故。三者智大;由人法二无我一时通达故。四者勤大;由三大阿僧祗劫无间修故。五者巧大;由不舍生死而不染故。六者果大;由至得力、无所畏、不共法故。七者事大;由数数示现大菩提大涅槃故。”(注26)此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行大与巧大。行大是具足自利与利他行;巧大是不舍生死而不染,即是不舍生死烦恼,但亦不为其所染著。生死烦恼实是就世间而言,不舍生死烦恼,其实是不舍世间。故行大与巧大,都是不舍世间之意。
七、不舍世间的特色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说,大乘思想的特色,在于不舍世间这一精神方向,或生活态度。这当然是与小乘思想相对比而言。我们不说这是大乘的本质,那是避免读者误解大、小乘各有不同的本质之故。我们认为,大、小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从《缘起性空》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都求解脱。它们的分歧,是在对世间的态度方面。
这不舍世间的态度,可以说,贯通著一切大乘经论,而尤以大乘经为然。上面提到的《维摩经》,可以说是最显明的例子。它的名句,如“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注27),“菩萨于生死而不舍”(注28),“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注29),说的都是这个态度。

另外,唯识宗的涅槃观,也有表示这种态度之处。按《成唯识论》论涅槃,分为四种: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有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无住涅槃。(注30)《成论》解释最后的无住处涅槃谓:
“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辅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槃。”(注31)此种涅槃,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利乐有情”与“用”,都表示不舍离世间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