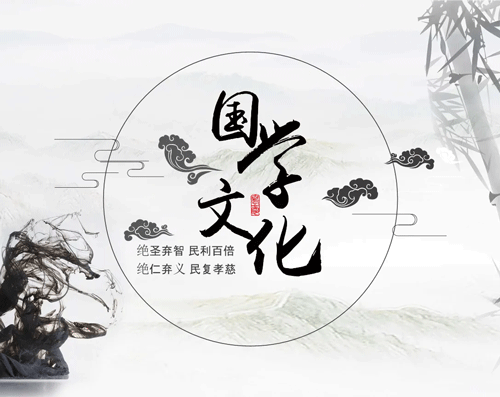释道宣的佛教表现艺术思想和理论贡献
发布时间:2023-10-08 10:04:04作者:大悲
唐道宣是继梁僧佑之后在佛教表现艺术的理论和历史记录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据《宋高僧传》卷第十四记载:
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后,府君陈吏部尚书。……九岁能赋,十五厌俗诵习诸经。依智頵律师受业,洎十六落发。……隋大业年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于终南仿掌之谷。[1]
道宣(596—667)原籍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另记载为吴兴湖州人),俗姓钱,其父在陈朝曾任吏部尚书。隋朝初年佛教大兴,于是15岁赴长安,在日严寺慧頵门下受业,翌年剃度为僧。其后在智首门下修习律学。智首是一代律学宗师,“钞疏山积,学徒云涌”,后来成为最高僧官的灵裕,也曾在其门下听受讲习。道宣的律学基础师承有门,应运而起,在当时研习律学的浓郁风气中成长为佼佼者。
道宣生平“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精持戒律,闻名遐迩。“宣之持律声振竺干,宣之编修美流天下。是故无畏三藏到东夏朝谒,帝问自远而来得无劳乎?欲于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时常闻西明寺宣律师秉持第一,愿往依止焉。敕允之。”[2]善无畏(公元637~735)唐代高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甘露王的后裔,十三岁继承焉荼国王位,后出家,向达磨掬多学习密法。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善无畏以八十高龄抵达中国长安,玄宗拜以国师之礼,奉诏住兴福寺南塔院,后移西明寺。翌年,奉诏于菩提寺译经,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为密教传至中国的先河,与后来的金刚智、不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共同奠定中国汉传佛教中密宗(又称唐密)的基础。道宣在律学和文史两方面的成就,远及西域,声震天下,公元716年,道宣已经过世,但是从天竺远道而来的善无畏法师还是慕名要求依止在他曾经驻锡的西明寺。道宣是在乾封二年(667)十月三日逝世的,年七十二,僧腊五十二。“高宗下诏令崇饰图写宣之真,相匠韩伯通塑缋之,盖追仰道风也。宣从登戒坛及当泥日,其间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3]“先所居久在终南,故号南山律宗焉。”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律宗就因道宣多年在终南山修习、创建律学而立宗,称为南山宗,并称他为南山律师。
道宣“撰《法门文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录》《羯磨戒疏》《行事钞》《义钞》等二百二十余卷”,他的律学成就集中表现在阐扬“南山律学”的五大部疏钞中,包括于武德九年(626)撰成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作十二卷),贞观元年(627),撰成的《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贞观九年(635)撰成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卷、《疏》二卷,随后又撰《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贞观十九年(645)撰成《比丘尼钞》三卷(今作六卷)。他在自序中评价自己所撰的律学着述:“包异部诫文,括众经随说,及西土圣贤所遗,此方先德文纪,搜驳同异,并皆穷核;长见必录,以辅博知,滥述必剪,用成通意”[4],应该说是毫不夸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道宣的主张不仅受到当时佛教界的广泛推重,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佛教。
由于戒律、戒学涉及僧众的威仪,举凡衣食住行,无一不涵盖其中,与本书揭示的佛教表现艺术息息相关,因此,道宣引起本书关注的,首先是他在这方面的有关着述。显庆二年(656)道宣撰成《释门章服仪》一卷。龙朔元年(661)又撰《释门归敬仪》一卷。乾封二年(667)二月,他在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他所制的仪规为诸州沙门二十余人传授具戒。同年他撰有《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一卷,《律相感通传》一卷。此外他还撰有《释门正行忏悔仪》二卷、《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卷等。
一、道宣在戒相论述中体现的佛教表现艺术美学观念
《释门章服仪》一卷撰于显庆二年(656),《释门归敬仪》一卷撰于龙朔元年(661),都是道宣晚年的作品,集中体现了道宣通过对戒相的要求所体现出来的佛教表现艺术美学观念。道宣是继道安之后对中国戒相影响最大的高僧,也可以说是佛教表现艺术的重要理论家。
道宣在《释门章服仪》中指出:
原夫道隆下土,纲领一焉。理则廓纷累于清心,事则显嘉相于形有。良以正道玄漠,长劫之所未窥;灵胤昭彰,含识于斯攸仰。是知,鹿园创启,鹤树终期;开萌济世之模,昌示容光之迹。剃染之异,变俗习之生常;量据之仪,必幽求于正捡。且四含八藏,难用备寻。一袭三衣,何容昏晓。既是释门常务,无时不经,义匪妄存,事符真教。固使住法万载,唯承形服之功;出有三圣,咸祖前修之业。
道宣认为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形象对修为素养的影响十分深刻。他认为,佛教在世间传播,纲领只有一个,佛法义理的最终功效是净化心灵,而佛事活动则需要显现一种美好的现实的形象。伟大的真理玄妙而悠远,一般人难以明白,但是以形象加以显示,却可以使众生仰慕恭敬。因此,释迦牟尼在一生中开创普度众生的事业,也到处留下了光辉的印迹。出家众剃发、染服装,是为了对社会习俗加以改变以示区别,服装的裁制,一定要认真探讨达到正确的标准。这些佛门的日常事务,随时都要符合经典,其内涵不是可有可无,做事必须符合真正的传承。他把形象的作用提得很高,甚至认为既便佛法在世间延续万年,形象即形体和服饰的功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道宣在《制意释名篇第一》对制订僧侣服装形象的重要意义专题阐释:
形服之所感人,怀生务本;道法之所回向,启化初源。故释父逾城,途经林泽,行见猎者服以袈裟,便脱宝衣,贸得麤布僧伽梨。即而服之,成正觉道。及开化也,若自若他,创染玄纲,先乘此服。故善来声发,俗衣变而成法衣。八事随身,如善见说,羯磨等受,先立形同正仪。故律云:彼剃发着袈裟,与出家人同,此诚证也。斯何故耶?良由非变服无以光其仪,非异俗无以显其道也。括其大归,莫非截苦海之舟航,夷生涯之梯蹬。故《贤愚经》云:服此法衣,当于生死疾得解脱。故梵王布化存生而立运通,释尊垂范亡我而捐罪福;倾五住于心尘,排二死于内外者也。
道宣认为,形象服饰之所以感人,在于剃这种发式、穿这种服装的人能悲悯众生,立足根本;而佛法传播的趋向不是背离人间,而是启动教化,阐扬根本。他追述了僧侣服装的来历,是释迦牟尼在成道的过程中将“俗衣变而成法衣”,并创立规矩,使剃发和着袈裟成为僧侣的两大特征。两大特征的重要价值是:“非变服无以光其仪,非异俗无以显其道也”。服装的样式和色彩,是佛教仪礼中至关重要的必备因素;与俗众相区别的目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彰显佛法教理。佛教徒的最大目标是“了生死”,而“服此法衣,当於生死疾得解脱”。法衣能够使人在生死轮回中尽快得到解脱,法衣的作用之大,发挥到极致。这些观点清晰地表明,道宣是把服装、形体都作为一种彰显思想的表现形式,甚至要求达到能以其艺术度化众生的高度。
因此,道宣在《立体拔俗篇第二》论述了理事僧俗的关系,其实际落脚在对“形服”的评价之上,他认为:
今人行道,事理两分。言事则俗习未亡,寻理则真心体附。斯则强分二谛,有凡圣之殊途。故张两仪,无去取之恒式。致使于衣知足,务在无瑕;事清心净,便怀入道。故十种遗弃之衣,世情所舍,三圣服之无厌,道仪所归。观事无异俗之嫌,涉理有资神之用。斯则挹酌二谛。
他批评了“事理两分”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通病,就是许多信徒在理论探讨方面很真诚很倾心,但是一接触实际事务,世俗的习气就无法摆脱。这就是真谛与俗谛的分裂状态,使凡人与圣人成为两条道上的人。道宣认为,在从“言事则俗习未亡,寻理则真心体附”向“观事无异俗之嫌,涉理有资神之用”的转变过程中,如何改变对十种“遗弃之衣”的审美是关键。“于衣知足,务在无瑕;事清心净,便怀入道。”“无瑕”、“心净”,前者观物,后者观心,审美的改变,最终是“服之无厌,道仪所归”,达到真谛与俗谛的圆融无碍。
道宣渲染了形服变化后氛围的剧变:(胜德经远篇第三)“幢相既立,则群鹿安神,鸟王怀怖,龙子保命,恶鬼潜形,人见生善,即其事也。况能祖承正教,受用得仪,近则随行自修,远则资成圣业。” 形服变化不仅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而且有助于自修和成圣。
道宣对服装颜色进行了细微的考察和论证,他引经据典,强调“坏色”,即“当以三种青黑木兰随用,一坏成如法色。”“ 色非纯上。绝于奢靡”。(《法色光俗篇第四》)他还对裁制方法作了记述和阐释:“故服此衣,且条堤之相,事等田畴。如畦贮水,而养嘉苗。譬服此衣生功德也。佛令像此,义不徒然。故律云:五条十隔者是也。至于条数多少,堤量短长,各有诚文,如别所引。”(《裁制应法篇第五》)对于服装细节的内涵,他也给予说明,例如:
在《方量幢相篇第六》中指出:“袈裟无领标解脱之衣,钵盂无底表难量之器。”袈裟没有领子,体现这是象征 “解脱”的衣服;钵盂没有平底,表明这是不可限量的容器。服装与器物都被赋予宗教的意蕴。
此外,道宣在《释门归敬仪》中对佛门礼仪进行了专门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具有历史记载的价值,而且流传久远,像道安的《宪章》一样,至今仍在佛教徒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是一段活化石。例如,他认为:“归信威仪,入道之始,不可隐略。”可以有助于“内长信心,外生物善”。
佛门礼仪,很重要的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渊源。道宣在行文中明确指出:
俗中《周礼》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官。斯非内教,然礼贵从俗故也。
一曰稽首拜,谓臣拜君之拜也。稽训为稽(计奚反)即久稽留停头,至地少久也。
二曰顿首拜,谓平敌者如诸候相拜也。即以头叩地,虚摇而不至地也。
三曰空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即以头至手,所谓拜手者。
四曰振动拜,谓敬重之战栗,动变之拜也。
五曰吉拜者,谓拜而后稽颡,谓齐衰不杖以下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与吉拜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后作稽颡。颡是额也,以额触地无容仪也。
六曰凶拜者,稽颡而后顿首拜。谓三年服者拜也。
七曰奇拜者,谓先屈一膝,即今时所谓雅拜也。一说奇拜但一拜,以答臣下之拜也。
八曰褒拜者,褒读为报,报拜者,再拜是也。又云,褒拜今时持节之拜也,即再拜于神与尸也。
九曰肃拜者,但俯下手,今时揖者是也。亦指妇人拜。又肃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余则再拜之。
上并俗礼正文,郑康成依位释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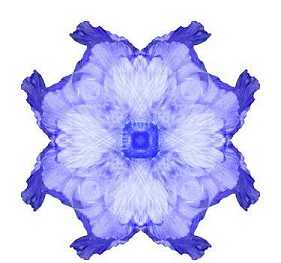
道宣认为:“斯非内教,然礼贵从俗故也。”以上的礼仪并非基于佛教,但是“礼贵从俗”,必须对佛教落脚的中国国土民俗表示尊重。在列举了中国传统礼仪之后,道宣着重指出,与中国世俗传统礼仪有所不同的是源自古印度的佛教礼仪,道宣列举了十二项,并一一加以阐释,这些礼仪对中国佛教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悠长,具有至今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南无稽首敷坐具脱革屣
偏袒五轮着地头面礼足右膝着地
胡跪一心合掌右绕曲身瞻仰。
“南无”,是流传至今的佛教用语,道宣考证说:“初言南无者,经中云‘那谟婆南\’等。传梵讹僻,正音盘淡,唐言我礼也,或云归礼。” “南无”是音译的讹传。道宣从其内涵解释为:“归亦我之本情,礼是敬之宗致也。”也就是说,以“归”,即归顺、归随、归属、归附,表达个人归向、信奉佛教的心情本意,而以“礼”来表现达到极点的崇仰敬重。
道宣举例说:“天竺设敬,先以身礼,后以颂叹。如《无量义经》:八万菩萨来诣佛所,头面礼足,遶百千匝,散华烧香。以衣宝璎珞,并钵器百味,充满盈溢,色香具足。又设幢幡轩盖,众妙妓乐,处处安置鼓作众器而供养佛。即前互跪,合掌一心,俱共同声,说颂赞曰:‘大哉大悟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着。天人象马调御师,道风德香熏一切。’如是等颂有三十余章。……据其行事,应在拜后。”按照古印度的礼仪,先以身行礼,再以唱诵加以赞美。“南无”应是在礼拜之后的唱诵。
道宣对叩拜的礼仪详细进行考证:
二明稽首者,古文为稽,今则为稽。俗所常行,不必从古。《白虎通》云:“稽者至也,首者头也,言下拜于前头至地。”即《说文》云:“谓下首者为稽也。”《三苍》云:“稽首,顿首也,谓以头顿于地也。”然今行事“顿首”为轻,谓长立顿首于空也。故晋时释慧远与俗士书,但云顿首而不揖也,谓非是曲身而但立也。故长揖司空不必身曲。然顿首、顿颡,俗中恒度。首,头之总名;颡,额之别目。然古仪有稽首稽首、顿颡顿颡,上敬天子殷重之谓。故重言之准此,顿颡,以额至地而拜也。
由于概念内涵的差异会导致行为的错乱,因此,道宣不厌其烦地加以考据,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纠正了当时对“顿首”的理解,相当于现在的挺身而立点头致意,与“以额至地而拜”相差甚远。
第三明敷坐具、第四明脱革屣,两点有共同性,因此道宣合而论之。他依旧对比论述了中印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差异,引申礼仪随之发生的变化。觐见尊长要脱鞋,在印度是必须的,而在中国,如果是在大庭,可以不脱,但是古代上殿时也要脱鞋除剑。道宣对安排“坐具”进行考证,认为当时中国僧人在礼佛时命令侍者安排坐具,是不合法度的。他推崇西方僧侣的作法:“今见梵僧来至佛前礼者,必先褰裙以膝拄地,合掌长跪,口赞于佛,然后顶礼。此乃遗风犹在,可准用之。”因此他制订准则:“ 以事详准,随时设礼,不可待席。有则从席,无则从地,可也。”[5]
同样,由于气候的差异,导致服饰礼节的变化,因此出现是否袒露右肩的第五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了解整个亚洲各国佛教服装样式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理解,样式的不同确实与气候和传统习俗有关,而其中共同之处又确实贯穿了由于佛教的基本信仰信念而导致的特殊要求。但是对于远在唐代的道宣来说,他要说服别人,就要引经据典,要以印度僧人为榜样。看来道宣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批驳了当时“割破襦子以为两片,号为襦袒”的作法,认为“安以衣遮,名为偏袒?”“ 仍有衫襦非袒露法”。他主张最高的崇仰仍要以袒露右肩来表现:“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极也。”[6]不过,从当代中国汉传佛教的礼仪来看,道宣的主张并没有被接受,这恐怕不止是气候的原因,其中,中国传统礼仪对“肉袒肩露”的回避应该是主要因素,特别是宋明以降,礼教盛行,中国人的审美发生巨大变化,在许多衣冠楚楚的士绅施主面前,本应极度庄严的大和尚却是“肉袒肩露”,那是社会习俗审美所难以接受的。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的僧侣,民国之前都统称“番僧”,对于他们的“肉袒肩露”,汉族的社会是视为异类的,其中不乏感到怪异同时又有所轻蔑之意。
第六项是“五体投地”,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的成语,说明影响之广泛深入。“五体”原称“五轮”,因为《阿含经》记载:“二肘二膝并顶,名为五轮。轮为圆相,五处皆圆。”道宣描述了印度僧人行礼的姿态和过程,特别是“两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两只手掌要反过来朝向天空,表示承接佛陀或尊师的双足。他同时批评了模仿这个姿势的某些生硬作法,违背了表示敬意的本心,是不可取的。[7]
与“五体投地”接近的礼仪是第七项“头面体足”。这是印度礼佛的最高礼节。道宣认为在表示尊重方面,中外有共同之处,即“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者”,最生动的例子就是中国历代相沿的尊称如“足下”、“陛下”、“殿下”,都是“有所称谓,不敢及形”。所不同的是,中国内地表示敬重,要求距离很远就行礼拜,或者说尊贵者是不容许接近的,既便是恭敬行礼也要有一定距离,而古印度的最高礼仪是贴近尊贵者、手捧双足以额头触足,甚至以面颊贴在足背上。[8]
第八、九项肢体礼节涉及跪拜,“明右膝着地”,其实不止于右膝,对于有关礼仪几乎作了全面阐释。由于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以右手按地降伏天魔的,因此命令所有弟子要以右膝着地。另外还有“互跪”,是专门用于悔过的礼仪姿势。对比丘尼而言,照顾她们体弱,容许其“长跪”。不管哪一种跪拜,都要依照礼仪严格执行,否则,像经典中指斥的“骆驼坐”之类的姿势,不仅不能祈福,反倒获轻慢之罪,甚至遭到沦落畜生道的业报,事态就十分严重了。[9]
第十项肢体礼节是“一心合掌”[10],看似简单,依照道宣的解释,却蕴含着深意。合拢十指手掌,目的是“敛束其心,不令驰散”,所谓“掌合而心一也”。这既是向佛陈言时的礼节,也是以恭敬心作为对佛的供养。在具体表现过程中,不仅要“开指而合掌修善行”,而且连站立的姿势,也要“敛指而开跟”,就是足尖收拢,足根略分,以示恭敬,而不能足根收拢,足尖分立,像八字形状。道宣认为,这些礼仪虽然似乎是小事,但是“渐渐依行,心性调柔,方可论道。”道宣的观点似乎可以概括为:道无不在,道存乎礼,礼既显道,游而趋艺。合十合掌,关乎大道,成乎真艺。
绕塔、绕佛和曲身瞻仰,是佛教徒礼敬佛陀的一种表现,也是佛教礼仪中动感很强的一项内容,道宣对这两种动作礼仪的探讨有所引申。佛教经典中历来要求右绕,即面向佛塔或佛像,向左开步,然后右绕。因此,道宣称之为“天时”,即记录太阳运行的日晷指针投影的轨迹方向,俗称顺时针方向。不过,据道宣目睹印度僧人在长安的佛事活动中经行旋绕时,发现和上述的右绕恰好相反,是采取日月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的方向,因此,道宣称之为“天道”。道宣对天时、天道二者并无臧否。同时道宣探讨了绕行的匝数,发现在经典记载中并无确切要求,“或云一匝三匝七匝百匝千匝无数匝者”。因此,道宣归纳出一个道理:绕塔、绕佛,都无非是表达自己信仰的坚定而已,“总而言之,以敬为本”。为了表现敬重,就可能要不断重复;“故内外清信,来至佛前,礼而后遶,遶已复礼。加敬重沓,无得恒准。”虽然动作简单,但是不断重复,也就加重了对敬重的表现。这既是对礼仪标准内涵的一种探讨,也是对表现艺术审美观念的一种表述,即重复节奏在审美中的作用。[11]
道宣选择涉及肢体礼仪的十二种装束方式或动作方式加以阐释和探讨,对僧团的表现确实是既从宗教的立场加以规范,同时也从艺术的高度给予了深求。此外,“曲身低头,注目瞻仰,随心机用”,还有许多,不可能一一说尽,其基本精神已经阐明,可以一以贯之。
二、道宣在《续高僧传》中阐释的佛教表现艺术美学观念
《续高僧传》是道宣的重要着作,在第三十卷的《论》中,表达了他对佛教表现艺术的许多重要的美学观念。
首先是明确对表现艺术的重视。
忍界所尊,惟声通解。且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即世常行,罕归探索。今为未悟,试扬攉而论之。爰始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
他认为,只有声音,在现实世界中最受尊崇,因为只有靠它才能沟通理解。声音的流传变化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很少有人认真探讨。作为弘扬佛法的经师当然要以德为本,实际上要以声音表述内容,以便受众的精神受到启迪,甚至由于听到这种声音而皈依佛门。
道宣的观点,在近代从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再次得到印证。许多人注意到,为什么评书、话剧、电影、流行音乐乃至电视发展如此迅速?就因为在一个文盲充斥、便餐兴盛的社会里,靠听觉和视觉感官接受的传媒是最捷便的,而通过文字乃至思考才能获得的教益,往往被排斥或疏离。反话正说,也就是显示了声音和画面在现实社会中受到尊崇的地位是有社会基础、有理论依据的,予以充分重视,也在所必然。
其次,是考察对声音的处理应用,对何以为美加以探讨。
顷世皆捐其旨。郑卫弥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致使淫音婉娈,娇哢频繁。世重同迷,鲜宗为得。故声呗相涉,雅正全乖,纵有删治,而为时废。物希贪附,利涉便行。未晓闻者悟迷,且贵一时倾耳。斯并归宗女众,僧颇兼之。而越坠坚贞,殊亏雅素。得惟随俗,失在戏论。
从负面讲,对声音的应用不一定能够得其要领。他抨击错误的导向,是“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用哀伤委婉吸引关注,靠唱高调、甩高腔表现不同凡响。其实,正是这种作法导致“淫音婉娈,娇哢频繁”,声音的宛转变化失去控制,玩弄技巧不厌其烦,虽然一时之间得以风靡,但是对于听众是得到觉悟还是陷入迷茫,却全然不顾。“得惟随俗,失在戏论。”在得失之间权衡,只是单纯适应了世俗的喜好,却把弘法变成了游艺。“声呗相涉,雅正全乖”,背离了佛教表现艺术服务于弘扬佛法的根本宗旨。[12]
这种负面影响的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并非偶然,道宣回顾了陈思王曹植以降,从三国及至唐代的数百年历史:“且复雕讹将绝,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无一契。”本书在前文中对曹植的历史贡献曾专门论述,同时也涉及后世对他的高度评价。无论曹植如何,那一段记忆中的辉煌,随着岁月已然消逝,确是不诤的事实。
道宣对比了佛教表现艺术的优劣:
若夫声学既丰,则温词雅赡;才辩横逸,则慧发邻几。必履此踪,则轨躅成于明道;
未若高扬洪音,归依三宝。忽闻骇耳,莫不倾心。斯亦发萌草创开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素,开大施门。打刹唱举,抽撤泉贝。别请设坐,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至如解发,百数数别。异词陈愿,若星罗结,句皆合韵,声无暂停,语无重述。斯实利口之铦奇,一期之走捷也。
如乖此位,则滥罔翳于玄津。但为世接五昏,人缠九恼,俗利日隆而道弘颇踬。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对文人,学构疏芜,时陈鄙俚。褒奖帝德,乃类阿衡。赞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陈满月,则曰圣子归门,悉略璋弧,岂闻床几。若叙闺室,则诵窈窕从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动色。僧伦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谓福徒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炫唇吻,摇鼓无惭。艳饰园庭,闰光犬马。斯并学非师授,词假他传。勇果前闻,无思箴艾。遂即重轻同迹,真误混流。颜厚既增,弥深痴滞。宁谓道达,岂并然耶?至如善权之对晤储两,千纸不弊其繁华;真观之拔难程神,百句弥开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考,佳严审其郊邑。词调流便,奕奕难穷,引挽伦综,惬当情事。能令倨傲折体,儒素解颐,便识信牢强,颂声载路。今且略明机举,则得人开悟如此。有背斯言,则来诮掩化如彼。辄试论矣,临机难哉。
道宣生活在一个盛唐的伟大时代,他当然要呼唤一个伟大的天才,来开创或续写佛教表现艺术的新篇章。
道达之任,当今务先。意在写情,疏通玄理,本寔开物;事属知机,不必诵传,由乖筌悟。
故佛世高例,则身子为其言初;审非斯人,则杂藏陈其殃咎。统其朗拔,终归慧门。法师说法之功,律师知律之用,今且随相分位,约务终篇。俗有无施,不可又陈无备一人。道则不轻,未学亦开降外须博。是以前传所叙,殷勤四能,即用以观。诚如弘例,何以明耶?
三、道宣所记录的隋唐时代佛教表现艺术杰出人物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记录的,主要是南朝末年历经隋唐时代变迁的一代僧侣。这是道宣所处历史时期决定的,也先决地注定了这一代僧侣的一些共同特点,即面临时代变迁、政权更迭而不得不应对的巨大苦难。他们所呈现的佛教表现艺术,其中不乏在涡漩中生存的悲壮和凄凉。
道宣在《续高僧传卷第三十》中,特别设立了《杂科声德篇第十》,其中“正传十二选十附见八”,这些入传的高僧有下列人物:
隋京师定水寺释法称传三(智云)
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四
隋苏州栖霞寺释法韵传五
隋东都慧日道场释立身传六(慧宁广寿)
隋西京日严道场释善权传七(法纲)
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八(玄应智骞)
隋京师日严道场释慧常传九(道英神爽)
唐京师玄法寺释法琰传十
唐京师定水寺释智凯传十一
唐京师法海寺释宝岩传十二
道宣对本篇命名为《杂科声德》是有专门解释的,他认为:“自古诸传,多略后科,晋氏南迁,方关名实。然则利物之广,在务为高。忍界所尊,惟声通解。”在记载佛教人物的史传中,大多忽略以表现艺术弘法利生的类别。梁僧佑在《高僧传》中开辟《诵经》《唱导》两个科目时,也做过类似的解释。
[1]《宋高僧传》卷第十四
2]《宋高僧传》卷第十四
[3]《宋高僧传》卷第十四
[4]
[5]三明敷坐具、四明脱革屣者,中梵极敬。此土群臣朝谒之仪皆在殿庭,故履屣不脱。有时上殿则剑履皆舍。此古法也。天竺国中地多湿热,以革为屣,制令服之。如见上尊,即令脱却。自余寒国随有履之,行事之时,既脱足已,可践土地,应在坐具。寻讨经律,无敷坐具之文,但云“脱屣礼足”。今据事用,理须坐具,故制坐具。缘云,为身为衣为僧卧具。既为身衣,明知前设。又坐具之目,本是坐时之具,所以礼拜之中无文敷者。故如来将坐,如常自敷。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余人为敷。今见梵僧来至佛前礼者,必先褰裙以膝拄地,合掌长跪,口赞于佛,然后顶礼。此乃遗风犹在,可准用之。无坐具明矣。比有行敬在佛僧前,仍令侍者为敷坐具。此乃行憍,未是致敬。又有要待设席方始礼者,亦不可也。如见尊长,即须下拜,安待觅席耶?以事详准,随时设礼,不可待席。有则从席,无则从地,可也。如在清庙、阙庭、公衙之所,何有设席?以此准例,则敬慢两分。
[6]五明偏袒右肩。或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膊者,所言袒者谓“肉袒”也。示从依学,有执作之务,俗中短右袂,便于事是也。今诸沙门通着衫襦,少袒三衣者,遂割破襦子以为两片,号为襦袒。此则名义俱失,不可寻之。故行事时袒出一肩,仍有衫襦非袒露法。故《大庄严论》云,沙门释子者右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门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见长老乃偏袒之。安以衣遮,名为偏袒?一何可叹也。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极也。
[7]六明五轮着地者,亦云五体投地者。地持亦云,当五轮着地而作礼也。阿含云,二肘二膝并顶名为五轮。轮为圆相,五处皆圆。今有梵僧礼拜者,多褰衣露膝,先下至地然后以肘按地,两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今时行礼,观时进退。若佛像尊师,却坐垂足,方可如上五轮接足。如其加坐,则随时而已。亦见有人闻有顶足之相,遂致就坐,拔他足出,云我欲顶戴。一何触恼,又是呈拙。故知折旋俯仰,意在设敬,如是例知。
[8]七明头面体足者,正是拜首之正仪也。经律文中多云头面礼足,或云顶礼佛足者,我所高者顶也,彼所卑者足也,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者,礼之极也。如俗中重尊友者,不斥其名字相名为足下者,义类同也。又如天子太子有所称谓,不敢及形,或称乘舆车驾,或云陛下殿下,皆敬仪一也。然中边行敬其家不同,此土设敬远拜为重,天竺设敬近形接足拜乃为至极。故经中陈如久不见佛,来礼佛已,以面掩佛足上,斯则头面礼足之相具也。若闻诸佛功德,心敬尊重,恭敬赞叹。知一切众生中德无过上,故言尊也。敬畏之心过于父母、师长、君主,利益重故,故云重也。谦逊畏难,故云恭也。推其至德,故云敬也。美其功德为赞。赞之不足又称扬之为叹。随以一事至佛,其功不可尽也。
[9]八明右膝着地者,经中多明胡跪、互跪、长跪,斯并天竺敬仪,屈膝拄地之相也。如经中明,俗多左道,所行皆左故。佛右手按地以降天魔,令诸弟子右膝着地。言互跪者,左右两膝交互跪地。此谓有所启请,悔过授受之仪也。佛法顺右,即以右膝拄地。右[骨*委](退罪反)在空,右指拄地。又左膝上戴,左指拄地。使三处翘翘,曲身前就。故得心有专志,请悔方极。此谓心随其身,行慢失矣。今行事者都无思审,径至佛前,加趺坐地者、右[骨*委]着地者、两膝并坐者,经中名为“骆驼坐”也。此并身既慢惰,心亦从之。来欲请福,反收慢罪。既乖礼意,又增慢习。一成苦业,兽中报受,可不思哉。故律中请悔或蹲或跪,文自解云:跪者,谓尻(苦高反)不至地,斯正量也。僧是丈夫,刚干事立,故制互跪。尼是女弱,翘苦易劳,故令长跪。两膝据地,两胫翘空,两足指指地,挺身而立者是也。经中以行事经久,苦弊集身,左右两膝,交互而跪。经中比丘亦有两膝至地白佛者。言胡跪者,胡人敬相,此方所无,存其本缘,故云胡也。或作胡跽者,捡诸字书,“跽”即天竺国屈膝之相也。俗礼云:授立不[起-巳+危],[起-巳+危]谓屈膝,俗所讳之。凡有所授,膝须起立。
[10]九明一心合掌。律文或合十指爪掌供养释师子者,或云叉手白佛者,皆谓随前缘而行事也。莫不敛束其心,不令驰散,然心使难防,故制掌合而心一也。今行事者掌合不得,以事校量,心坚硬而散乱也。将欲反源更始,须加功用。当开指而合掌修善行,不得合指而开掌从恶习也。又两足据地,多乖仪节,敬俗不立,况行道乎。亦须准前十倍努力,当敛指而开跟,如敬俗流。不得敛跟而开指,作八字立,令无识者笑也。斯言苦楚,斯事现行,万失不觉不[打-丁+王]滥也。有心行者,既睹斯文,抚臆论心,一何纵诞。固当如上准酌,渐渐依行,心性调柔,方可论道。道在清通,无系无我。如何存着,反立慢根。用此日生,深非生寄。门门指掌,庶或可观。
[11]十明在绕恭敬者。经律之中制令右遶,故左行绕塔为神所诃。左遶麦[卄/积],为俗所责,其徒众矣,且述知之。今行事者顺于天时,面西而北转,右肩袒侍而为敬也。比见有僧非于此法,便面东而北转,为右绕也。天竺梵僧填聚京邑,经行旋绕。目阅其踪,并从西回,而名“右转”,以顺天道,如日月焉。然捡经中,匝数无定,或云一匝三匝七匝百匝千匝无数匝者,斯何故耶?皆谓随务缓急,致有不同。莫不身曲掌合,徘徊瞻不,不能已已。周旋敬重,申己信重之心也。故内外清信,来至佛前,礼而后遶,遶已复礼。加敬重沓,无得恒准。总而言之,以敬为本。故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知,礼与其敬,宁重。重则随心,显晦万途,其致一矣。故孔门赞素王,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也。
[12]《续高僧传》卷第三十《论》